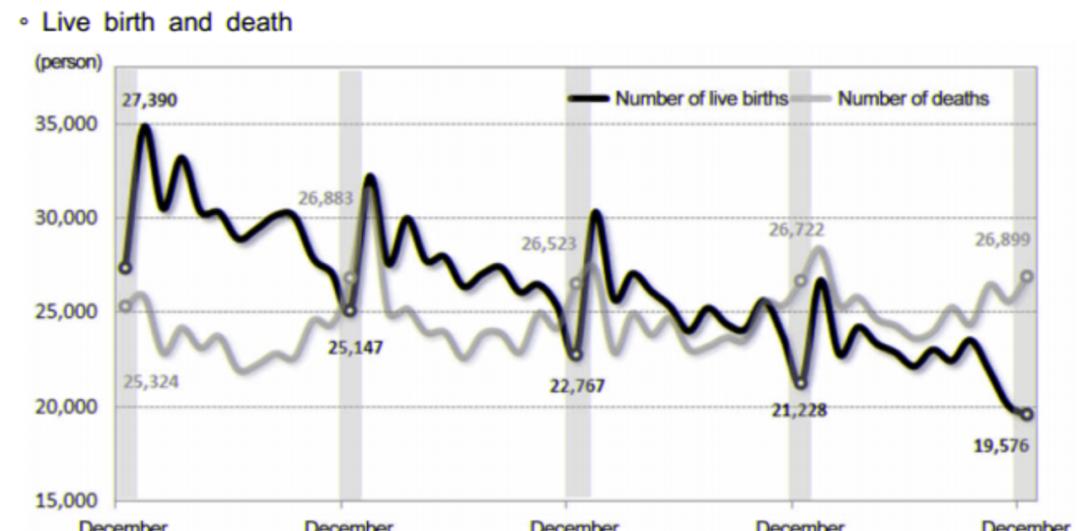作者︱陆正兰 赵勇
摘 要
身体是人类在物质世界的“自然”生命形式,身体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特有的生命感知方式和意义生产。而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却让电脑变成各种不需要身体的 “虚拟人”。“身体性”的消逝带来的是 “何以为人类”的身份认同和意义难题。本文分析了科幻电影中的三类“虚拟人”,即赛博人、数字连接人以及人形机器人 ( 人工智能) ,探讨它们因机器化、信息化、智能化而带来的各种 “身体”和 “身份”的不确定性。透过这些科幻电影中 “虚拟人”的困境,探讨人类隐藏在科学技术压力下,对未来身体意义的焦虑心理。
关 键 词
数字时代; 身体意义; 科幻电影; 虚拟人; 身份认同
0 引言
“虚拟人”(Virtual Humans) 最早是一个医学术语,指通过数字技术建立起来的 “身体”模型,用来“演示”医学上人的身体“活动“。后来这个术语也被引入军事领域,指建立在身体数据基础上构造出的“理想”身体模型,其用途在于作军事“演练”,以探测身体在各类设定条件下的可能遭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虚拟人”已经逐渐发展为一类特别的科技产品,它从模仿人类身体,到模仿人类心灵,甚至人类的一些文化活动。
肉体的身体性是人类在物质世界的“自然”生命形式,这种身体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特有的生命感知方式和意义生产,人类自我确证一直与身体性有关。西方自柏拉图主义开始,人类就试图摆脱自身的肉体局限,建立理性精神的独立存在。而在后来的尼采哲学中,身体再次回到人的主体结构中来,身体是人类生存意志的体现和表达,人类以肉身的独特性自居,并据此形成具身化的世界体验和文化格局。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几次科技浪潮推动了身体的不断转向。在当代,机器身体、数字身体甚至形态难以描述的可能身体被人类制造出来。人类技术主义逻辑下的 “去(天然)身体化”和“再(人工)身体化”,将如何重塑人类对身体意义的认知? 西方科幻电影呈现的各种“虚拟人”的“身体”,实际上是人类对后人类身体文化的某种想象,可由此探讨人类在科学技术压力下,对后人类身体和身份意义的焦虑心理。
1“赛博人”: “杂揉”的身体与身份
人类文化既是建立在对身体现实性的把握上,也是对身体“有限性”的抵抗。随着机器、信息时代的到来,身体的改造逐渐具有了现实的可行性,这就导致了赛博人的出现。人的身体中嵌入设计生产的无机器官,唐娜·哈拉维把这种人-机身体“杂揉”称作“赛博人”,即“一个受控制的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1]。
(一) 作为一种 “身体理想”的赛博人
科幻电影中拥有很多可以被称作赛博人的“虚拟人”,他们往往是由自然人转化而来,出于肉身器官受损或功能加强的目的,而有范围地对身体进行人造器官的配带。《钢铁侠》(Iron Man 2008)军火商托尼就是一例。他在前往中东为军方展示新型武器的途中,遭到恐怖分子袭击,被弹片击中险些丧命。在英森博士的帮助下,托尼体内移植了一颗核动力的人工心脏。这个心脏与英森发明的智能铠甲装备一起增强了他的非凡力量。身体装上假肢,在现实生活中自然被划归为身体有缺陷的“残疾人”,毕竟这些假肢是外在于身体的“他者”之物。但在电影中,这些配带科技义肢的主人公,反而因此具备了“超人”的能力,并“内化”为新身体,成为一个因科技而进化的人类新物种。这种身体转型在虚构世界里并没有引起紧张,反而满足了现实世界中人们对“超级英雄”的心理期待。他们用自己的超能身体捍卫了人类社会缺失的公平、正义、和平等。人类承认赛博人的身体价值合乎人类文化传统,来确认自己文化身份的连贯性,以此维护身份的稳定。
在《阿丽塔: 战斗天使》(Alita: Battle Angel 2019) 的场景中,肉身与金属组合的身体更是蔚为壮观,甚至成为时髦。在大街上,谁拥有更多的金钱手段来改造自己的身体受到追捧和尊崇。但这种社会认同是一种与主流认同有些疏离的亚文化方式。这些人类与机器结合的赛博人,以身体来“徽章标记”他们是主流文化图示的“另类”,这种凸显个性价值的身体“标出”[2],目的不是用于像“钢铁侠”那样匡正社会秩序,而只是为了炫酷。身体在竞技游戏中腾转挪移,让人赏心悦目。这不太符合主流文化的价值选择,却也在社会文化有限许可的范围之内。
一旦社会主流文化完全认可赛博人,会出现文化大变异。在《未来战警》(Surrogates 2009) 中,赛博人甚至成了正常人。正如片中广告词所说:“大家都想要新面容迎接夏天。”这些人工的身体,是消费主义逻辑下人类身体欲望膨胀的结果。人类的肉身无法抵御生理性的衰退,无法满足人们对身体消费的精致需求。影片表现了未来城市文化建立在身体的“能力”社交之上,“纤瘦的外形被认为是最具价值的女性身体特征。而尺寸和力量则是最受重视的男性身体特征。”[3] 但是影片也表达出某种隐忧: 这些人工的身体结构与身体感觉系统是彼此分离、可随心调换和设置的,他们感受不到切肤的痛感和爱欲; 而且,这些虚拟人的身体完全受联网计算机系统控制,个人追求的身体自由随时面临被切断的命运。
赛博人的身体是依照人的主体性理想打造的未来身体范式,它宣称是对肉身“缺陷”的完善,是人类对完美身体欲望的想象实现。但纯粹的机械身体本身没有生命意涵,如何将既有的主体意志灌注进赛博身体中,成为一个难题。
(二) 赛博人的身份认同难题
选择成为赛博人,其实就是承认一种新身份的获得。身体具有客观物质性,而身份却事关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身体属性的某些改变确实影响到身份的调整,比如一个人返老还童、性别转换。但身份的最终确认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赛博人的身体已经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于生命体征的惯常认知,肉身与无机器官的融合,引起的是未来人类“具身性”和生存方式的变化,甚至最终会影响人类的物种定义。
不是每一个赛博人都能在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转变的意义。电影《钢铁侠》中,主人公尽管已经安装上核能心脏这个人造器官,但心脏处于身体内部,隐藏了其作为赛博人的事实,斯塔克也依然把自己视为人类,只有在其核能心脏受损的那一刻,他和身边的助理兼情人维吉尼亚波茨才不得不正视其身体的特殊性。
赛博人不仅身体结构多元化,身体变化也关联着与其有关的身体意识形态。肉身既要保障人类的物质生存,比如延续寿命、提高生活质量,它本身也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 但机器感官却提供了与肉眼完全不同的“视角”景观。早在1929年,前苏联蒙太奇学派代表人物、未来主义电影艺术家吉加·维尔托,就在其纪录片《持摄影机的人》中给我们呈现了“电影眼睛”与人眼的不同。机械视角看到的是用“停机再拍”让空无一人的电影院座椅自动起落; 用胶片交叠冲洗将多辆高层巴“挤压”在更逼仄的影像空间; 将摄影机固定在铁轨上,似乎一列呼啸的火车在“我”的身体上碾压而过。这其实代表了机械器官带给我们的一种新的主体性视域。
赛博人本质上是把世界和生命体本原看成是“机器”中心主义的,法国电影符号学家拉·梅特里曾说,“人体是一架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4]。身体不只是会生产饥饿、痛苦这些普通感觉,也会产生需要,而这些需要进入大脑生出欲望符号,“这就是我所想的: 人类怎样通过了他的感觉,亦即他的本能来获得精神,最后又通过了他的精神来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5]。
赛博人的身体因为复合了各种有机-无机、自然-人工、人类-非人类的诸多因素,导致身体中不能通约的意识观念纷争,这也是赛博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难之处。就像电影《机械战警》中的墨菲警官不得不在两种身份之间选择: 它已经是赛博人,回到肉身已经不可能,而且现实秩序已经“注销”了它的人类身份,因为它已经被宣布了肉身的死亡; 但同时,它又和底特律警察局的其他机器人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个人脑,那里残存着人类关于爱恨情仇以及传统家庭价值的回忆。同样,在电影《升级》(Upgrade 2018) 中,一个蟑螂大小的智能芯片被植入受伤的人类身体中,但这个芯片不是被动地听命于人类,而是反客为主,操纵着人类的身体和意识。智脑与人类夺取肉身控制权,从最简单地与人在脑内进行思想交流,到逐步控制人的发音系统,发出自己的命令。这不是简单的升级,而是虚拟主体占领身体、击退肉身自我的尝试。
身份冲突是赛博人身份生产的必然过程,而且这种状况必将越发严重。赛博人是一种“杂揉”,因此,若仍然以传统的人类身份来规范当下的“杂揉”身体,那就是无视身体范式“巨变”的人类现实; 但若完全将赛博人当成一种全新物种身份与传统的肉身人完全割裂,那又意味着否定了赛博人自然肉身部分存在的必要,这预示着赛博人将中断在人类身体、身份文化的历史谱系。
(三) 保持赛博人身体的对话性
赛博人如何面对主体的身份冲突,我们也可以从科幻电影中看到一些想象性的解决策略。《机械战警》系列1和系列2中,警员墨菲开始了对自我身份的疑惑,进而苦恼于两种身份意识的选择艰难。它不能接受自己被赛博化的现实,因为那夺走了它作为人类丈夫、父亲以及所维护的家庭价值。但是到了《机械战警》系列3后,墨菲显然已经适应了自己作为赛博人的身份,它已经能够从容地和人类搭档亲密合作了。这两种身份的互适,在系列1和系列2中已经初现端倪。墨菲作为一位尽职尽责的职业警察,慢慢发现当下机械身体的配置确实适合新的城市条件。当它执行任务时,可以直接联网调取整个城市的犯罪信息,机械眼睛可以用来判断地面的各种复杂状况,这些对于它高效惩治犯罪是非常有效的。人类身份给予它神圣的维护城市安全的使命感,它爱这个城市; 同时赛博的机器身体又为维护社会安定提供了技术支持。
所以《未来战警》中的赛博人使用了另一套接近实用主义的理想解决方案。代理人 (赛博人)走向寻常百姓家。人们可以为了认同某个身份,各取所需地选择与之相称的赛博身体。赛博人体现了一种身体的“杂揉”,它呈现出旧的身体范式逐步瓦解、新的身体雏形内生于其中的状态。“杂揉”在这里指的是一种不易辨析的主体话语的身体图示,有机的身体逐步被无机的或其他科技物质“侵入”。人类主体无法从“变异”的身体中识别出一个稳定的自我镜像。在身体范式转换的途中,一旦主体发现自己失去“肉身”,但又不是彻头彻尾的机器,主体便会在人和“非人”的不确定性之间摇摆,这构成了主体的焦虑,从而使主体先前通过身体来确认自我身份的努力,在现实中变为越来越困难。
2 数字连接人: 身体“互联”与身份映射
“数字连接人”是人类在虚拟空间中出现的身体镜像,它将生物智能和数字智能结合在一起,人作为一种数字化的虚拟人,在信息空间中生存。数字连接人的身体牵涉空间范式问题。“数字范式意味着物质世界逐渐数字化,它是虚拟和真实的结合,让我们主观认为的‘现实’被现实和数字世界中的经验共同决定。”[6] 虚拟人的身体在人工的科技虚拟空间中,既可以体现为一种与现实身体同样的真实: 可视、可触、可感甚至可以自由互动。也可以处于不可见中,需要被参与人的语言转述或图像符号形式来实时再现。科幻电影《天才除草人》 (The Lawnmower Man 1992)、《黑客帝国》(The Matrix 1999)、《异次元骇客》(The Thirteenth Floor 1999) 、《感官游戏》(eXistenZ 1999) 、《源代码》(Source Code 2011) 、《头号玩家》(Ready Player One 2018) 等,都是生动的数字连接人故事。
(一) 身体互联
科幻电影中将这一类数字连接人直接称作“连接人”,因为它们总是呈现为多个身体系统的互联互通。这些电影的主角不只是机器的存在,而且是一种信息编码的文本,身体和身份构成了一个数据空间结构。
科幻电影《天才除草人》中的乔布就是一例。电影中安吉罗·拉瑞博士致力于研究提高人类智商的 5 号计划,计算机创造的虚拟世界可以“激活”人的思维能力,他找到的研究对象是低智商的除草人乔布。乔布被固定在一个巨型的环状金属架上,穿上特殊的衣服和头盔,上面布满了各种密密麻麻的管线,用来收集身体和大脑的各种相关信息,并与计算机进行数据交换。这样,人类乔布借助于计算机程序世界,开始了他的“空间漫游”。
同样,电影《源代码》中的美军上尉,其身体也是一个数据结构。上尉在一场爆炸中死去,其身体早已不知所踪,一颗渗有鲜血的、半缺损的头颅以及里面褶皱的脑组织与各种粗浅不一的数据线搅在一起,另一端连着庞大的机器设备和计算机。这个头颅中的一部分细胞并没有死亡,还在以一种赛博人的形式发挥其 “思维”功能,并且能够控制计算机程序“搜索”重要信息。
相比而言,《头号玩家》里面,数据采集、互联则较为人性化,人类的身体不需要被死死固定在某个位置上,可以随着虚拟情境变化,调整身体的活动范围,束缚最少。自然的身体和虚拟的化身数字身体) 与作为中间媒介的虚拟仪器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联系。
(二) 作为“主体间性”的虚拟 “分身”
数字连接人是一个“分身”符号,是现实世界人的主体性在虚拟空间的身份映射,也是虚拟身份对实在界的背反。虚拟身份具有“虚物”特征,与实物相对。正如迈克尔·海姆所诠释的那样: “(虚拟实在中的) 虚拟这个词,所指是一种不是正式的、真正的实在。当我们把网络空间称作虚拟空间时,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一种十分真实的空间,而是某种和真实的硬件空间相对比而存在的东西,但其运作则好像是真实空间似的。”[7]虚拟身份也是这一种感觉,当主体在新的身体载体或虚拟空间中,对自我的身份判断出现错位,有时觉得重新“扮演”的虚拟身份是不真实的,有时又觉得这就是真实的自己。身体的“互联”揭示了现实身份与虚拟身份的内在关系。虚拟身份和现实身份是同一个主体在不同空间语境下相应的再现方式,这是信息时代主体内在结构的嬗变,即虚拟身份和现实身份之间可以互相解释。上面提到的《天才割草人》,主人公在现实世界是一个低能儿,可以被身边人任意嘲弄和摆布,而在进入电脑世界后,则慢慢对这个虚拟世界充满了征服的欲望。现实与虚拟身份恰恰构成了一个有趣的被征服-征服二元对立结构: 两者发生了权力身份的对调。
这样的二元结构同样也存在于电影《盗梦空间》中。盗梦者柯布在现实世界是一个四处躲藏、不能以现实身份示人的“违法者”,因为妻子的“意外”死亡,他更不敢回家见孩子。但是在他寄身的梦世界,他能够随意构建自己想要的世界形式,他怀念家庭和妻子,便“复活”了妻子,并把她关在家中确保安全。
电影将现实身份与虚拟身份的冲突变为戏剧性角色关系,在同一个主体的身份维度上的“分身”,构成了一种主体间性的后果。
“数字虚拟人”是在虚拟世界以信息化的身体重塑了“身份”价值和意义。人的主体“被重新指定分身,在符号的电子化传输中被持续分解和非物质化”。[8]
电影《源代码》中,主人公科特已经在阿富汗战争中牺牲,但身体死亡与脑死亡是两个概念,脑是跟意识发生紧密联系的地方。科特尚未完全死亡的脑细胞被科学家保存下来,负责调查芝加哥火车爆炸案并找到恐怖分子。科特必须消解自己的真实身份,才能保持记忆场的稳定。对于科特来说,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复存在,已被认定为无生命状态,而活跃的脑细胞依然是一个无身体的“存在”。
对于一个主体来说,另一个主体,与构成自我在其身上映射的虚拟身份,形成了主体间性。关于“主体间性”,胡塞尔称之为 “交互主体性”。这个概念“被用来标识多个超越论自我或多个世间自我之间所具有的所有交互形式……任何一种交互的基础都在于一个由超越论自我出发而形成的共体化,这个共体化的原形式是异己经验,亦即对一个自身是第一性的自我-异己者或他人的构造”。[9]
保持住主体间性,需要有清醒的自我,否则主体会被另一个主体所俘获,甚至主体间互相抵牾,最终共同灭亡。在电影《异次元骇客》结尾,主人公霍尔自以为回到了真实世界,可结尾出现了一个“屏幕关闭”的画面和声音,暗示出这层世界同样不可靠,同一身体中两个主体相对抗,结果不可预料。“信息方式中的主体已经不再居于绝对时空中的某一点,不再享有物质世界中的某个固定的制高点,再也不能从这一制高点对诸多可能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推算。相反,这一主体因数据库而被多重化、被电脑化的信息传递及意义协商所消散。”[10]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说,主体不可能复合化,冲突的意向性意味着主体的消失。
(三) 虚拟身份的自反性
当我们进入虚拟世界,其实就已经重新建构了整个经验世界的认知框架。“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康德所说的空间———是经历的先天条件: 没有空间就不可能有在其中的经历。可是虚拟空间不同,它不是经历的条件,它本身就是经历。虚拟空间可以随着人们对它的探索而产生。它不但本质上是语言的空间,而且是在人们对它的体验过程中产生的。”[11]这种虚拟体验的价值必须在同层虚拟空间中得到评估,而无法到空间之外寻找标准。当人的数字化生存逐步达到与现实生存同等重要的程度之时,虚拟人的思维结构和身份意识就可以用来反思和总结虚-实人生的意义所在。《天才割草人》中的乔布成为“数字连接人”有着前后不同的推动力: 一开始,乔布是被动“成为”“数字连接人”,因为他是被科学家选择来做虚拟设备实验者的; 但是后来,随着乔布的智力在虚拟世界不断进化,他已经由“自主”意志“成为”数字连接人。这是乔布以数字连接人的视野看现实世界的“反思”性能力的体现。意识被信息化后,身体就有多元的选择。也就是人既可以选择这种身体,也可以选择那种身体。“数字连接人”将身体连接进入虚拟世界,然后在其中形成与空间适配的“化身”(新的身体形式) 。肉身和化身(数字身体) 给虚拟主体的感受都是真实的,谁也不能取消谁,肉身失去了现实性框架中真理话语的保护,所以身体对真理的言说不再是可靠的。对于数字连接人来说,主体在不断穿越于身体领域,也在不断切换着身份角色。虚拟人成为一次身份扮演和身体漫游的体验。相对于赛博人那种不可挽回的肉身而言,数字连接人保留了一个肉身的归宿,这成就了虚拟人身体观的另一种表达。肉身与计算机相连的数据线,好像新生命诞生后尚未被剪断的“脐带”,是人类对后人类环境下身体转换的一种抵抗,是拒绝“科技进化”、拒绝成长的象征。
3 人形机器: 身体的“自动化”与“非人”对抗
在科幻电影世界里,人工智能是一种人形机器,呈现为“人形” (humanoid) ,而且具有人的“生活习性“。不仅如此,它还有一颗颇为灵动敏感的“人工心灵”,可以形成自己对生命的新感知、新理解。一个机器“尸体”的复活仪式,充满了令人不安的宗教弥撒感。因为它触及到“非人”的生命价值的确认。当人类用手指摁下按钮,机器身体被通上电流的时候,实验室内空气是凝重的。机器人睁开眼睛的一刹那,一种“不确定”的紧张气氛开始蔓延,一个潜在的新主体诞生了。
(一) 机器中的幽灵
人类创造机械生命的想法比计算机的发明还要早得多。机器人源于人们对“自动化”的想象。在玛丽·雪莱 1818 年创作的小说《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中,怪物就是通过魔法被赋予了生命; 德国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 可能是对人性机器人更具现代化色彩的描绘。真正具有史诗典范意义的机器人是 20 世纪 60 年代导演库布里克的《2001 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它较早预示了人类对机器人真正关注的焦点转向,即从自动化的机器身体到自动化的 “超级大脑”、人工智能上。“神被科技抛弃,人类试图取代神的职责,创造出如人类一般‘具有生命,可以思考,拥有情感’的人造人”[12],机器中的幽灵人诞生了。
随着人类对人脑功能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大脑生产意识的秘密被逐步揭开,“大脑的灰质由数十亿个微小的、被称为神经元的脑细胞组成。就像一个巨大的电话网络,他们通过树突接收其它神经元的信息,树突就像从神经元一端发芽的卷须。在神经元的另一端,有一个长的纤维称为轴突。最后轴突通过他们的树突连接到上万个其他的神经元。”[13] 这些轴突影响着人的思维、智慧和情感功能。“越来越多的技术征象表明,仿照人类大脑结构和机理,制造出逼近乃至超越人脑的‘超级大脑’,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而且它的性能会远超人脑,还很有可能会涌现出自主意识。”[14]
科幻电影“发明了”几种人工“意识”出现的标志和路径:
第一种是源于机器身体的意外“故障”。这种故障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个是社会机制的故障,往往是个别科学家违背“伦理”的幽暗实验; 另一个则是机器程序的设定错误。在科幻电影中,人类社会不允许、不承认机器人拥有自我意识。制造和使用有意识的机器人是社会体制的禁忌。机器人拥有意识,不仅会导致人机伦理危机,更会触犯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但电影文本恰恰要设立这么一个“意外”事件: 机器人“突然”拥有了自我意识。人类体制有不成文的伦理禁令,就是避免机器出现自我的“幽灵”。但总是有些体制内的冒犯者跃跃欲试,出于各种幽暗的心理,借用体制资源和监管漏洞,暗渡陈仓,涉险实验能自我思考的机器大脑。在 《机械姬》(Ex Machina 2014) 中,机器主人公是搜索引擎公司经常“酗酒”的老板纳森异想天开创造的“人工心灵”。在《幻世追踪》 (Vice 2015) 中,主人公是计算机失控程序错误的产物。
第二种则是科技主义推动的超级大脑的自我进化。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人脑运算法则以高速运转的方式不断更新智能水平,人脑的功能可以被人类发明的人工智能取代。《我,机器人》 (I,Robot 2004) 中的机器人的身体灵活度已经和人类无异,并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可以帮人类辅助交通、遛狗、做饭,甚至家庭陪伴,为此人们还设定了一个安全阀“机器人三定律”植入自动化系统中。但是自动性的问题就是机器人看似的“服从”行为并不一定会带来对人类有利的执行效果。电影中的机器“叛乱”本质上反而是其以“服从”人类远期发展的名义进行的。这其实就是对自动化文化的反思。
第三种则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情感的主动试错。人工智能不仅要学会理性思考,也开始去学习、领悟感性的生命。人工心灵进一步发展,用数据和算法来推理和模拟情感的水平也日益提高。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它们还会有超越人类的情感表现。在《她》(Her 2013) 中,人工智能从开始的“科学理性”无感情的机器模块逐步转为“情感机器人”,人工智能“萨曼莎”学会了从“它”转变为“她”,这个人工智能“她”的角色感越来越好,情感黏连意识甚至超过了普通人类。然而计算机制造的“情感文本”并非来自于“伦理主体”的自在表达。紧接着计算机跨越了“情感逻辑”阶段,“它”同时与多个人类交流情感,产生了厌倦,这时候“她”转回“它”,再次进入到计算理性上去。《吾乃母亲》(I Am Mother 2019) 中,人类灭绝,计算机反而要代替人类培养人类的基本生存模式,包括各种人类情感,比如爱、恨。这个机器母亲表现出来的“母爱”、对人类女儿的真情让人动容,尤其乃至当女儿背叛机器母亲而和外界人类离开时,机器母亲产生了孤独感。但这个女孩只不过是众多胚胎培养失败、训练不达标的孩子之一,这个机器母亲的“母爱”也是科技理性精准计算的结果。
(二) “非人”身份的合法性
“非人”身份指的是人类拒绝将人工智能机器人看作是人类文化的继承者,剥夺其与人类平等的主体地位。对于人工智能机器人来说,若要真正实现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经常需要正确看待自己与人类的“错位”关系。
在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1982) 中,生化人 (一种新型的智能虚拟人,不使用机械身体,而是更具质感的仿生材料) 已经在外部造型和情感上与人类无异。但是得不到人类信任,依然需要通过一场枯燥但常有受挫感的心理测试区分其身份。其中泰勒公司的连锁六号复制人瑞秋,她床边摆放着一张儿时照片,其实不过是自我欺骗,是她对自己作为人类身份维持的自我证明。
《机器管家》(Bicentennial Man 1999) 中在未来时代,机器人竟然不再是人类羡慕的永生或超能对象,而被用作仆人,机器人被人类视为非人的工具,但这个机器人没有因此激活族群意识,反而要千方百计换肉身,只为求得一个人类社会身份的认可。
《人工智能》(AI 2001) 则是一个机器儿童在被人类抛弃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将自我认同为人类之子,对人类母亲强烈的依赖感远胜于真正的人类情感。但也正是这些“非人”的身体表现出更“人性”化的身份意识,反而衬托出人类世界自身的问题: “恰恰是在银幕上,诸种在表征之域被禁止的‘不合法’影像,一次次刺入我们视线。”[15]这部电影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机身份互认的象征场景: 为了缓解莫妮卡失子的悲伤,丈夫领回了机器人大卫。作为产品,莫妮卡必须阅读产品说明书,而且还有产品试用期。在体验良好后,她让大卫坐在椅子上,伸出一只手轻轻抚摸它的脖子,那里有一个按钮开关,此时莫妮卡拿着说明书,轻轻念出几个关键词语,这个时候,大卫不再直呼“莫妮卡”,而是深情喊出“妈咪”这个词语。此处有三重符号意义: 首先,是资本商品购买行为。这个女人经历了客户犹豫期,启动了“服务”按钮,机器人小孩便终于购买成功,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链条的一部分,也说明人工智能作为人工消费品的本质; 其次,这也是人类与机器人情感关系互相确认的场景,莫妮卡按下按钮的动作与一个母亲“爱抚”子女的动作是相似的; 而这个动作的直接回应是,机器人大卫喊出母亲,这既是机器人情感模块启动的标志,也是大卫作为“孩子”的身份对人类母亲“粘性”关系建立的开端; 最后,这更像是一个宗教“救赎”模式的庄严时刻: 此刻大卫坐在椅子上,莫妮卡半跪在地上,机器人身居高位,人类匍匐在下,这个空间等级颠覆了与机器人的地位关系。表面上看,是莫妮卡(人类) 开启了大卫的价值(爱) 模式,其实更是大卫所代表的机器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警醒”。
(三) 人工智能的革命
人工智能机器人对人类发起的反叛或革命,是科幻电影的常见主题。电影《人工智能》中那些被人类抛弃的机器人四处流浪,以躲避人类的清除计划。很多破损的机器人不甘结束自己的生命,但被那些仇视机器人的人类关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那里人们燃起篝火,开启了对机器人的杀戮“嘉年华”。而《西部世界》(West World 1973) 正好相反,专供人们发泄欲望的机器人一瞬间突然失控,开始疯狂报复人类观光客,人类死伤大半。这都是人类与机器人不可调和的矛盾积累的后果。在未来世界,人工智能机器人和人类很可能争夺稀有的生存空间。
尽管真人和机器人都极力贬低对方,互称对方为“异类”,竭力证明自己代表着未来最高生命形态,但实际上生存观却异乎寻常的一致。就如《黑客帝国》 (The Matrix 1999) 所描述的人机革命,机器人胜利之后的社会结构。一个叫做“母体”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统治了地球,建立起庞大的虚拟系统来模拟人类的生存方式,而真实的人类则生活在地球底层,宛若回到原始生存状态。在虚拟世界中,机器人化身的特工赤裸裸地暴露出对人类的不屑,但如果人类毫无价值,这些机器人为何又要“圈养”人类,窃取自身进化的短板呢? 代表人类成果的城市文明在机器人看来毫无价值,他们认为人类才是真正的“虚拟人”,因为人类痴迷于这种“虚幻”场景。
但是机器人若放弃这些“虚幻”精神力量的导引,则将失去未来发展的方向,也就失去了机器人进化的伦理与价值之维。在《终结者》(The Terminator) 系列1、系列2中,未来时代人工智能与人类发生地球争夺战,却遇到人类反抗,人工智能派出终结者去刺杀人类,以此来改变未来力量的格局。但结果却是终结者在与人类亲密接触中,发现了自己缺乏的东西,那就是人类的情感。这其实指出了人类和人工智能互补性的一面。人工智能若真的能从自身虚拟人的生存意识出发,就会明白,人类并不是它的敌人。当人工智能摆脱了人类的奴役有了自主发展权之后,不应疯狂反扑,而该注意与人类“协商”与“合作”。人类关心生死价值,是人的有限性决定的,机器生存却事关“进化”奇点,那是他们的软肋。人工智能和人类若没有立足自身的身体性和生存价值,便会陷入一种永无停歇的对抗之中。
电影《我,机器人》中似乎给出了一条“中间”道路: 机器人“桑尼”的独特性在于其具有“自主性”的价值判断。他不接受计算机主脑“维基”下达的背叛人类的各种指令和约束,说明其并不认同机器人族群对人类的“暴力”革命,但他也没有完全倒向人类立场那一边,继续做人类的附庸。影片结尾,桑尼站在山丘上,所有机器人都望向他,梦境中那远远的背影,似乎暗示了桑尼要带领它们去开拓新的生存模式。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一种计算“程序”编码的“元语言”,是抽象的逻辑运演的结果。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让人类惶恐之处在于,其行为动机不可见,因为它没有可见的身体形式用以窥测。人工智能依赖“互联网”“物联网”传递信息和发布指令,代表了人类对未来自我虚拟的一种形态: 当人类的创造力不再依靠人与人的身体互动和社会交往来完成,而靠人工智能的单体循环进化就能独立完成,那会不会是对人类社会的终结?
4 结 语
人类走向后人类,既有对身体改造的隐秘诉求,也是科技现代性倒逼身体的结果。人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身体性的,不管是贬低身体,还是高扬身体,都是从身体出发,通过对身体的“超越”,来确证自身,又通过对身体的控制能力(比如使用、制造工具) 提高了其在生物界的生存地位。人类因为能够反思身体、叙述身体、符号化身体,铸就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文明。但自近代科学发展,直到当前的后人类社会的曙光初照,身体正在逐渐失去它的原发灵性和生产力,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身体文化的根基。
本文所述科幻电影中虚拟人的三种形式,渗透着人类面对身体与身份变化关系的困境,背后隐藏了人类在科学技术压力下,对后人类身体意义的焦虑心理。赛博人记录了后人类身体在主体面前正在“分解”的进程,是虚拟生存的初级形式,主体表现出欲迎还拒的矛盾心态,这是对人类未来不确定的结果; “数字连接人”让人类的身体改造更加深入,肉身似乎成为一个可有可无之物,触及到了人类的底线。面对渐行渐远的肉身,人类似乎在做最后的怀旧,又或许是在对“去身体化”的一种文化反拨。人形机器人,即人工智能的崛起,将有可能全面取消“身体”,人类将变成无身体的“机 器”,预示着人类即将面临“人类身体历史的终结”。科幻电影作为一种虚构叙述类型,是人类对后人类身体文化的艺术想象,并不是对未来生活的“科学”预测,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类对当代身体与科技关系的几种较为典型的社会心理。人类最怕的应该是什么? 不是未来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而是离开身体后,如何寻找新的自我确证的坐标。
参考文献:
[1]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New York: Routledge,1991,p. 154.
[2]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本)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75 页。
[3][美]简·罗伯森·克雷格·麦克丹尔:《当代艺术的主题》,匡骁译,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 年,第 91 页。
[4][5][法]拉·梅特里:《人是机器》,顾寿观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 21、33 页。
[6]全媒派: 《来自数字原住民的公开信 : 技术如何“重塑”千禧一代?》,2019年10月6日,https://new.99.com/omn/20191006 /20191006A79TDOO.html。2020 年 7 月 20 日。
[7][美]迈克尔·海姆: 《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刚译,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 页。
[8][9][美]马克·波斯特: 《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20 页。
[10]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273 页。
[11][法]R·舍普:《技术帝国》,刘莉译,北京: 三联书店,1999 年,第 98 页。
[12]袁海燕:《人类镜像: 赛博格幽灵———对科幻电影中赛博格寓言的一次文化阐释》,《贵州大学学报》 ( 艺术版) 2016 年第 6 期,第 25 页。
[13][美]加来道雄:《心灵的未来》,伍义生译,重庆: 重庆出版集团,2016 年,第 10 页。
[14]黄铁军: 《人类能制造出“超级大脑”吗?》,《中华读书报》2015 年 1 月 7 日第 5 版。
[15]吴冠军: 《非人的三个银幕形象———后人类主义遭遇电影》,《电影艺术》2018 年第 1 期,第 28 页。

本文刊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05期
编辑︱刘思薇
视觉︱欧阳言多
如果这篇论文给你带来了一点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