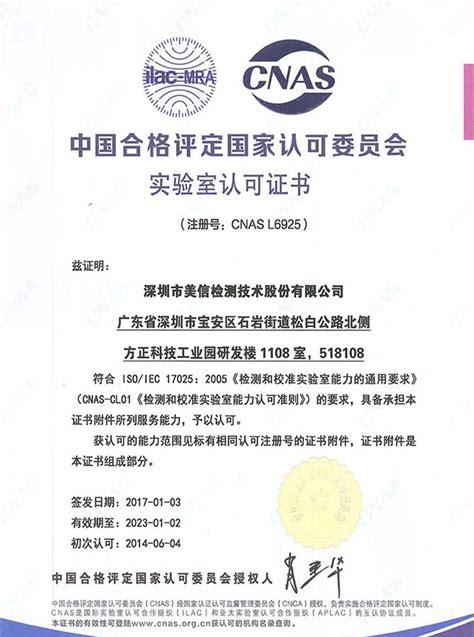我的母亲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她认定的事情,再怎么变都不能让她动摇。
她没有多少文化,一出生就赶上日本人连天的炮火轰炸卢沟桥。我的姥姥是一个小脚女子,带着七个孩子流亡,等到生活安定下来,母亲只有上扫盲班儿的份儿。匆匆认识了几个字之后就参加工作。等到我们兄弟五人相继出生,她的工作也就时断时续的进行。因为她得用手裁制剪缝出一家人的穿戴。她的固执就表现在她以自己的肢体当尺寸。
如果郑人是“宁信度,不自信也”,她则反其道而行,只相信自己。把尺寸装在身上,搁在心里,衡量着衣帽的大小及其他事宜。
她的一捺就是半尺,即后来的五寸,食指最里一节是一寸,小臂关节至食指间是一尺。我刚出生时高一尺五寸,她扯了二尺长二尺半宽的红布,给我做了件舒舒服服的小内衣。又扯了三尺半长,四尺宽的红布给我做了件小被,把我严严实实的包起来。在哥哥身高五尺的时候,母亲比划着哥哥已长到她的额顶,决定给哥哥做鞋。得用一捺半,再加一个手指的长度,做出来果然正正好好。
父亲有年冬天说有些冷,母亲给棉裤添了四两棉花。把裤腰让出一寸,父亲也不喊冷了。还直说添了棉花也不显臃肿,还这么合体,怎么量的这么准呢?
对此我也很好奇,曾问过她,别人做衣物都用皮尺量一量。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当时数学正在讲着度量衡。尺叫做市尺,三市尺是一米,一千米就是一公里。一公里是2里。1米等于十分米等于一百厘米等于一千毫米)。你为什么不用米尺去量一量啊?她说不习惯米尺换算。再说,就这么几个人儿还能对你们的身体情况没个尺寸?
母亲的尺寸早已了然在心。若不是对家人的细心观察,体贴关爱,是做不到了如指掌的。
自此喜欢上了有尺寸的日子。尺寸不只在量身高,腰围,鞋长这些具体的东西,更在于丈量一些看不见的事物上。也因为尺寸的存在,而让我由懵懂变成了明了。
得寸进尺告诉我,欲求应有度。一寸能满足,不要奢求成倍而变得贪婪。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则指导我,人或事各有其长处和短处,要充分了解自己。也要充分了解它人,彼此都有可取之处。有这个觉解,我不曾自轻自贱也不曾傲气冲天。
尺壁寸阴则告诉我要擦亮眼睛。尺璧不足以为宝,一寸光阴才是值得千方百计去争取的无价之宝。的确,有谁曾让时光倒流过吗?无论你多么强悍与伟大。
进寸退尺则告诉我,不要贪图眼前小利,否则会贪小便宜吃大亏。
尺幅千里则告诉我,不要看事物的外形小,但包含的内容很多。你看,一尺长的图画能把千里的景象都画进去。
至于寸草春晖,谁会不知道它所包含的感激之情呢?
更为神奇的,则是方寸之木,高于岑楼。一个人做事,如果没有分寸和标准。不把二者放在一个标准上进行比较,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荒谬到视一个被放在高楼顶上的寸木比高楼还要高。
“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早在两千多年前,睿智的古圣先贤已告诉我们,看待事物心里要有尺度,不可乱了方寸,做下惶然愚蠢的事儿。
母亲虽然文化不多,祖祖辈辈熏陶渐染。尺寸分寸,恐怕早已成为基因。生存在记忆之中,对生活的方方面面,拿捏有数,进退有度,操持有术。眼瞎心不瞎(不识字的人被叫做睁眼瞎),如是才能从容的走过人生的一场又一场风雨。
可是,尺寸是什么时候从我的生活中溜走的呢?市尺变成尺或米的时候吗?我当时不清楚,老师为什么要让我们学会这样的换算。只是米取代了尺,寸变成分厘毫的时候,我的脑袋就记不住有关尺寸的教诲了,因为我早已乱了分寸。在那么多铺天盖地而来的新概念中,我仓皇地记住一些考试必考的词,不知其为何意,却被告知,这是国际单位制,我们只有与国际接轨,才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
只是愚笨的我,尽管牢牢的记住了这些国际单位制。也没有感觉到与国际接上轨。年已半百,我连国际什么样还没有看到呢?倒是有一些影星,被称作国际影星,我似乎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些国际的影子。国际可能要求袒胸露乳及多次结婚离婚。除此之外,国际如神龙,只现一鳞半爪,不见首尾。这让我的生活,一塌糊涂,完全不靠谱。
没了尺寸没了分寸。我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冬天穿着短裤,把绒裤穿短裤里面。冬行夏令。虽然抓住了时尚的尾巴,可也抓了一身的病,因为我区分不了冷暖。
我冲进地铁里,庆幸抢到一个靠门的好坐,完全不管一旁的老太太看我一直用白眼球儿,因为我心里没有了老幼的区分。
我看到网上有人骂某某政府以权谋私,理所当然的认为它定会以权谋私。跟帖转发扩散该消息,因为我观念里没有真假。
我来到街头。看某国民众抗议政府为自由而战,心里羡慕人家的自由民主化程度高,而我丁点儿自由都没有,因为我不清楚这个概念的里外。
我区分不了的,还有很多:轻重,远近,表里,明暗,虚实,浓淡,敌我,因为心里没数,因为一直望着国际。我也不知道眼下,我该如何清晰地,有条不紊地度过我的日日月月。
怀念有尺寸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