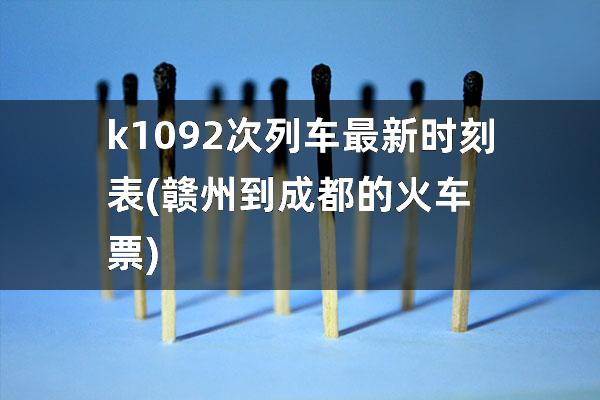今天这篇文章很长,不过读完你会发现这是和一个极其精彩的人的一场难得的深入的情感交流。
为什么而活的童年,N年前
我的闺女七岁了,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已经上三年级了。不是因为我是神童,只是因为我奶奶是小学教师。四岁的时候,爸妈每天上班,白天我就跟着奶奶。奶奶上课,我跟一个大姐姐坐在最后一排玩自己的,就这样玩了一学期,期中考试的时候,奶奶突发奇想,给我也发了一套一年级的试卷,没想到我一不小心得了双百。所以五岁起,我就开始正式上小学了。
我是个很内向的人(认识我的人,每次听我这么说,都恨不得拿鞋砸我),到七岁时还认不清楚全班同学,说过话的人只在前后三排范围内。七岁的黄毛丫头跟九岁十岁的孩子做同学,总是被大孩子瞧不起——没错,从小那个“豆包”就是我——这种弱小的被人嫌弃的豆包形象一直贯穿着我整个学生生涯。
学生生涯对我来说愉快的事情不多,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除了我自己,只有我的姥姥。姥姥是我整个精神世界的启蒙人,我对《山海经》、《拍案惊奇》、《七侠五义》的认识至今还停留在姥姥的故事时代。七岁那年,她告诉我,所有人都终有一死,我被这个念头吓坏了,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我都在想着这件事,晚上夜不能寐还在想。有一天晚上我被一个噩梦惊醒,梦里我躺在手术台上,无影灯全亮照着我的尸体(无影灯的样式跟白求恩那篇课文里的插图一模一样),我的爸爸妈妈趴在床沿上嚎啕大哭,而我漂浮在半空中看着这一切,心如刀绞。醒来的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阳台,透过窗户看到爸妈的卧室,他俩安静地入睡(隔着玻璃听不到老爹的呼噜),我在窗外泣不成声。
在极度的忧伤之中,我做了一件至今想起来都会后怕的事。我爬上阳台的水泥护栏,从五楼往下看,然后从护栏的这头走到那头,最后腿朝外在护栏上坐下来。那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议题神一般地进入我的脑子:如果人总是要死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在我脑中徘徊不去,一方面增加了我的焦虑,另一方面带给我一种莫须有的自信。在继续扮演豆包受到各种调皮男生的挑衅的时候,我都有了一个牛逼闪闪的利器,我有一个如此深奥重要的课题要思考,那些比我大的孩子们突然都变成了一群幼稚而不开化的蛮类。
我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在一次上学路上突然茅塞顿开了。再次,神一般的,一个念头钻进来,他说:你活着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因为你而快乐。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刻,我在红旗路和汉中路的转弯处,好像一道追光照着我,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观世音菩萨(额,看到这里,鸡皮疙瘩掉了一地的同学,欢迎发红包给我,多么排毒啊)。我僵立在路口,好半天才回过神,醒神后觉得无比开心快乐幸福满足,好像全身有用不完的爱要散出去。那一天,我见谁都傻笑,还暗自给自己一个约定,以后永远让人看到的是我的笑脸。
这个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人生之千里,往往起初差之于毫厘,不经意的一个小小的转念,可能就是人生路程的里程碑。
无处安放的青春,上世纪80年代
我青春时代最崇拜的人是我的大娘,她跟我一样属龙,比我大两轮。在那样一个封闭的年代里,她爱上我们那个地方的首席小提琴手,我的大伯,并且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她的身上有一种从来不受限制的热情和创造力,她藐视一切的规则,并且率性敢为,屡败屡战。她在个体户还可能被判投机倒把罪的年代里,一个人拉着板车卖甘蔗,并且大大方方地说她爱钱。果然,她凭借自己的才智在还不到四十岁时就成为了当地的首富。她很喜欢跟我聊天,每次都会不断地挑战我:“为什么不可能?凭什么做不到?”有一天她跟我说,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开一家自己的私人银行。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亮亮的。我妈刚好从旁边经过,听见她的话,不以为然地说:“你那些都是空想,根本就不可能,银行都是国家的,还能让你一个个人去开?”大娘只回了一句:“就算现在不可以,将来肯定可以的,规则都是用来打破的!”
然而大娘的梦想并没有实现,她是改革开放最早最快富起来的人,也成为骗子老千歹徒各种眼红者和穷亲戚的众矢之的。因为钱,她和她的亲人们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最后没有了钱,生活才逐渐归于平淡,可是那些流逝的时光,十几年的纠葛,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生命里。我再也没有见过像大娘那样明亮的目光。
我十五岁中专最后一年在大娘开的各种公司里实习,最开始是做火锅店的门迎,穿着红色的旗袍站在门口甜笑着说:“欢迎光临”。后来被调到保龄球馆做球童,那家保龄球馆是当地第一家,完全是在给市民做科普工作。球馆只有四条球道,因为简易所以没有引进自动化的垒球设备,全靠球童在幕后摆球。每次当警示灯亮起,我就要迅速地躲避来球,然后再迅速地把砸倒的球瓶按位置垒好。再后来我被调去做灯具店的库管,在仓库里清点库存,拼装灯具。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来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我成了一名灯具店营业员。我要记住所有灯具的型号、性能、优缺点,向进店客人介绍和推荐,客人付款后,要负责把灯具打包送客。
我跟店里的其他营业员关系都很好,她们教我化妆打扮,我们常常是一水儿的蓝眼影紫口红大金圈耳环高跟鞋的标准妆容,在生意清淡的夏日午后,嗑瓜子吃零食闲聊天。我不爱嗑瓜子,我爱吃苹果,就在我抱着一个大苹果奋力啃着的时候,我看见店门外一个女子走过,她穿着如今想来不算合体的灰色西服套装,全身散发着一种“白领丽人”的风采。我突然来了个闪念:我会不会有一天像她一样呢?
大时代的股海生涯,上世纪九十年代
93年7月13日,我跟二十多个青年男女一起到一家刚成立的证券公司报到,接受入职培训。那家证券公司租用了1/4的体育场通道,培训间歇我就跟另一个跟我年龄最相近的女孩静在通道里跑来跑去,像两只精力充沛的小鸽子。这些同事里我最喜欢老和,她有温婉的个性(当年),扮猪吃老虎的稳重,尤其是具有8秒一沓的点钞绝活,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记得有天陆家嘴突然飙升,水果糖大姐先扔进来一个报价单:“18块,追1000!”随后不断有人追高陆家嘴,最开始大学老师来卖出陆家嘴时还依然很有礼貌地对我说谢谢,后来越来越慌乱,他最后一次扑到我的柜台上来时,一丝不苟的头发已经凌乱了,声音也嘶哑了,大声对我吼着:“快快快,快看陆家嘴现在多少钱了?20?25买!全买!全部追回来!”后来我再没见过他们,也许是因为我被抽调到另一家新成立的营业部里筹建的原因。我在新营业部里主要负责国债期货业务,那时中国刚刚放开国债期货交易。一个早上,一对小夫妻神色紧张地提了一个大旅行袋来到营业部,打开一看全是10元面值的人民币(当时还没有百元面值)。收银员用了近2个小时才完成收银,十几万元,一笔巨款。快11点的时候,老公填了一张买多的报价单,递出单子的时候还对着左手边的老婆笑了一下。中午收市的时候,夫妻俩坐在营业部门口的台阶上,抱头痛哭。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也记不清他俩的长相了,只记得两口子的背影,和那男人被汗打湿贴在后背上的白T恤。
我第一次到上交所的时候,觉得非常失望,在我想象中,上交所是像华尔街一样的地方,交易员是最聪明的一群人,用各种肢体语言完成交易。可是上交所里的实景是每个人对着一部电脑,挂着个耳机,穿个红马甲,其实就是一群接线员嘛!327国债事件终于让我梦想成真了一把,我们所有做空的机构围着中经开一手举着合同,一手比划着成交价,大喊大叫地平仓。那一年,我18岁。中国的国债期货因327重创,被勒令暂停,一停就是18年。
退一步海阔天空,1997
国债期货暂停,我又回去重抄旧业做股票交易的老本行。那时我们公司原来的一个大户,已经越做越大,组织了一个操盘团队常年驻扎在我们上海的营业部里,他们的操盘手跟我们的交易员在一栋三层小楼里同吃同住同炒股。下班后我们常常几个人挤在机房里玩大富翁,500块一局,赢钱的负责晚上的娱乐和宵夜,输钱的负责陪吃陪玩。我每天的日程变成早上8点起床,食堂早饭后被司机送去上交所,下午3点闭市回宿舍玩大富翁,晚上八九点出洞玩到夜里三四点回来。这样的日子起初很令人兴奋,我们的身影出现在上海滩最新最豪华的娱乐场所,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们在不太喧闹的酒吧里,几个人一人拿一瓶酒却没有话说。
收到公司银证脱钩的消息的同时,我也听说我们在上海的营业部要转让给跟我们同吃住了两年多的大户,他们计划给这家营业部起名叫“德隆证券”。我那时已萌生退意,我把晚上花天酒地的日程改成去离我们最近的区图书馆,办了人生中第一张借书证。这之后的一年里,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泡在这间图书馆里,阅读了上百本外国小说。我发现我看书特别快,而且一看就不可自拔。我特别擅长看别人都说看不懂的东西,比如《百年孤独》、《尤利西斯》;我对外国人名特别不怵,什么希茨克利夫,什么芥川龙之介;我对小说里的故事特别感同身受,比如《幼师》里的战争的双方,比如《愤怒的葡萄》里被机械化剥夺了生计的农民。我时不时在同济的校园里溜达,虽然年龄与那些大学生相仿,但却总觉得自己已经老了,羡慕他们单纯的学生生涯。我决定回家上学,上大学。
鉴于我这么爱看外国小说,我一心想学比较文学专业,后来发现成人高考里没有这个专业,只好退而求其次地考了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只为了上里面的外国文学课。果不出所料,我的外国文学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后来又去读文博学院和行管院联合开办的博物馆管理专业,像听天书一样听了几年文物保护课,画了几年文物器物图。当我用六年业余时间换来一张学位证的时候,我证券公司的同事老周对我说:“文凭这个东西,没有的时候无比重要,有了以后一文不值。”
回到西安以后,我原来所在的证券公司已更名为银河证券。银河证券是由九家券商联合组建的,号称中国证券业的航空母舰,所以我们的LOGO好像一个红色和蓝色包围着的太极图,中间裹着九颗星。然而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过了没几年,银河证券就因为船大难掉头,又分家了。有天我路过银河证券,看到现在的LOGO还是那个红蓝太极,只是中间的九颗星星不见了。
插话:全斌同学(注:就是“二黑的爸”,公益人)勒令我走心地写出八千字来,我这一走心,写了四千字了,还没写到跟公益有关的事儿呢,这可怎么好!人年纪大了的缺点就是废话多啊。下面的四千字我保证留给公益事业!
丢手绢,找自己,2001
2001年的时候,我调到城市管理部,负责统筹三家营业部的行情咨询和广告业务。省台有一档叫《股市人生》的节目找到我,想要给我们的老板拍一期节目,老板竟然拒绝了,然后一伸金手指,说你给小廖拍吧。这个40分钟的专题片里里外外跟踪我拍了2天,让我跃然成为了好多亲友心目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那一年的9月11日,我刚打开电视扫视芒果台,突然看到画面一转,一段飞机撞楼的画面发出来,没有声音。紧接着凤凰台,央视陆续播出了特别新闻。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有些混乱了。这是真实的人生,还是美国灾难大片?这种分不清日月的感觉已经有一段时间夹裹着我了,在风起云诡的股市中,我每天早上跟股评师开会统一思想,心里却半点都不相信;每天过手着天文数字的钱,却想着这些年逐渐变成赌徒的一张张脸;每天目睹着别人的人生,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通向何方。我按照“别人家孩子”的套路演了二十多年,突然厌倦了,我要找找我自己。
第一次找自己的尝试是在那年11月。天气已经很冷了,我在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网站上发现一小撮人在召集去合阳观鸟。我问老鹳:“为什么要去观鸟?”老鹳说:“因为喜欢”。我觉得太酷了,这么多年我和身边的人都在做“对”的事,还没见过这种做“喜欢”的事的蛇精病,为了变成跟他一样酷的蛇精病,我克服了恐惧一切羽毛类动物的心理,准时登上了长途大巴车。
我的邻座是一个留着络腮胡带着鸭舌帽的小孩儿,虽然留着络腮胡,可一看还是个小孩儿。这枚小鲜肉一路上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了全球的资源被占有的形势,以及资源引发的安全问题和国家争端。他认为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疯狂掠夺,必然会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一路钦佩地听着他的宏论,心里想着:“乖乖隆的冬,这小孩儿将来是当米国总统的料啊!”我果断留下小鲜肉的名号和联络方式,他叫西北傻狼,大名李弘(编者注,李弘现任壹基金副秘书长)。
第一次的观鸟经历让我一发不可收拾。我在BBS上大量地发帖,写我的感受,然后跟群友们组织起各种各样的环保活动:去小学上环教课,去保护区跟着护林员巡山,去地标开展环保宣传。在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地里行走,在70度陡坡上相互协助着下山,在被树叶铺满的原始森林寻路,在一张脏兮兮的炕上挤着入睡,生活扑面而来。对比以前的人生,那时的我就像活在一个金玉铺就的牢笼里。我太爱这些人,太爱这些人带给我的生命活力了,尽管我们是网友,连彼此的真名都不清楚。
我们在一起有聊不完的话题,从城市的环保设施合理性到垃圾分类,从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到生物多样性,从环境保护到地球的寿命。除了这些,我们厮混在咖啡馆里,讲段子唱歌,更多时间是几个人在大街上边走边聊,有时竟是一整夜。跟业余时间比起来,白天在证券公司上班,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不知道为什么坚持的坚持了。
一头扎进这片海,2003
后来,我偶然认识了Jerome,他原本在上海YMCA负责一个外国志愿者在华服务的项目,后来因为外国志愿者希望能够到更偏远贫困的地区开展服务,所以他到西安来踩点。当时他还在犹豫要不要在西安设办公室,因为涉及到外国人出入境的问题,而他在本地几乎没有相关的社会资源。我果断介绍自己的同学给他,相关的手续很快落实下来,CCS(Cross-Culture Solutions)即将落户西安啦。Jerome问我:“你愿不愿意来CCS工作呢?”我愣住了。在我回复他的前几个晚上,我用SWOT分析转行与否的优劣和机遇,结果发现自己对跳进公益这片怒海之后的境遇一无所知,可是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那儿喊:“错过这个机会,你肯定会后悔!”
我在WWF网友聚会时宣布了我要全职做公益的决定,没想到不但没有收到鼓励和祝福,反而全是阻力和怀疑,他们说你这就是小姐脾气,不食人间烟火,你肯定干不了几天就受不了了。我想起不久前傻狼向我们宣布他打算退学去全职做公益时,遭到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的炮轰。为了这次转行,我在亲友间的指数迅速从“别人家的孩子”降到了“你可不要学”的水平。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包括我的双亲。
在CCS工作,对我最大的挑战是英语。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歪国仁的我在第一次要接待外国志愿者之前,认真地备了课,把经典的英语对话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当我打开房门,当四名歪国仁一起站起来向我伸出友谊之手的时候,我像瞬间被煮熟的大虾,所有的血都涌上头部,扔下一句“Sorry!”转身就跑,留下Jerome和四位歪国仁面面相觑。就这么磕磕绊绊地一路走来,我总觉得接待外国志愿者这件事跟我最初对公益的想象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是外国人来中国做公益,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做点什么事呢?在Jerome的支持下,我迅速构思了一个志愿者俱乐部计划,还请一位上海的网友帮忙做了网站,我们招募愿意参加志愿活动的市民参加俱乐部,一人一百的年费,全年可以免费接收公益资讯,参加公益活动。这个俱乐部的名字叫志愿之旅,第一次在《中国发展简报》上看到我们这个小俱乐部的名字时,我的自豪感那是岗岗的。
 这两次请假都是去参加自然之友的绿色希望行动。第一次是去陕西南部的汉阴县,一周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跟农村的孩子、教师同吃同住在一起,感觉好极了,完全符合我对做一名支教老师的全部想象,除了以前没想过不能洗澡这件事之外。这次环教活动结束后,我认认真真写了十几个教案发给自然之友,其中有一部分列入到《自然之友绿色希望行动环境教育教案集》之内。因为这次行动,我还获得了当年最佳环教志愿者的称号,次年,我受邀参加绿色希望行动优秀志愿者赴新疆开展环教。40天里,我们从于田各县到喀什疏勒,从疏勒到乌鲁木齐,一口气跑了20多所学校。除了给孩子们上环教课,我还被校长叫去给维族老师上汉语课。晚上住在老乡家,对这个原以为很神秘的民族有了切实的体察和接触。他们的淳朴、简单、对生活的乐观,对传统的尊重,对信仰的坚守,都令我大为惊叹。同时那些一触即发的民族矛盾,那些奇怪的民族政策,又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
这两次请假都是去参加自然之友的绿色希望行动。第一次是去陕西南部的汉阴县,一周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跟农村的孩子、教师同吃同住在一起,感觉好极了,完全符合我对做一名支教老师的全部想象,除了以前没想过不能洗澡这件事之外。这次环教活动结束后,我认认真真写了十几个教案发给自然之友,其中有一部分列入到《自然之友绿色希望行动环境教育教案集》之内。因为这次行动,我还获得了当年最佳环教志愿者的称号,次年,我受邀参加绿色希望行动优秀志愿者赴新疆开展环教。40天里,我们从于田各县到喀什疏勒,从疏勒到乌鲁木齐,一口气跑了20多所学校。除了给孩子们上环教课,我还被校长叫去给维族老师上汉语课。晚上住在老乡家,对这个原以为很神秘的民族有了切实的体察和接触。他们的淳朴、简单、对生活的乐观,对传统的尊重,对信仰的坚守,都令我大为惊叹。同时那些一触即发的民族矛盾,那些奇怪的民族政策,又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
新疆的绿色希望行动收官之前,我跟梁从诫先生和方晶老师在喀什的街头溜达,边走边聊,聊了很多。他说环境保护非一朝一夕之功,得看你们这些年轻人的,社会公民也要看你们的。临别前,方晶老师拉着我的手说我们都挺喜欢你,你要努力!后来我再去北京,时不时地去梁先生家里坐坐聊聊天。最后的一次去,梁先生已经不能聊天了。后来梁先生的追悼会我却没敢去,因为觉得愧对他们的善待,我总是不够努力,一条“鲁蛇”。
 和梁先生伉俪在新疆,2004年
和梁先生伉俪在新疆,2004年
鲁蛇的故事,2005
写到这里,其实心里有点难过。一周前在北京学习萨提亚课程的时候,听王行老师讲“鲁蛇(Loser)”的故事,想想自己,也是鲁蛇一只。人生中值得拿出来书写的事,似乎是成功的,但是在那些值得书写的成功之后是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失败。我们总梦想成功,其实谁不是对失败更有经验。
CCS的工作不能满足我对公益的想象了,我要更贴近那些受侵害的群体和事件,我要更直接地为他们做点事。在阿拉善和宣明会之间犹豫了很久,最后被老妈的一纸逼婚令留在了西安,加入了宣明会。宣明会据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益组织,让我想到了银河证券,果然我在宣明会也经历了收获与失望的三年。大型组织总有大型组织必有的优势和缺陷,无论是企业还是公益组织。我是应聘项目官员去的,应聘时还跟HR说最好派我去非洲救灾,结果我因为广告咨询的工作背景,被留在西北区域办做了Communication Officer。当时,Comm团队除了我,只有半个人Lisa。Lisa主要是BOSS的助理,其次才是Comm。后来,这个团队不断扩充,工作也越来越多。我的团队总是冲在最前面,团队成员干得很high,但拿到工资的时候又很不平衡。我发现一个问题,在公益组织里,干多干少是一样的,干得好跟干得糟也是一样的,并且干得少的和干得糟的总有办法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绩效评估主要靠忽悠。如果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那时候我再次错误地以为最大的就是最好的)组织的问题,那么别的组织会好吗?
那时我们还有一项很有趣的工作叫整简报,我跟Sissi在会议室里剪剪贴贴的时候,Sissi突然说,其实她很喜欢做这样的事,就是不用费太多脑子,简简单单从从容容地完成,偶尔做一天女工的工作其实是一种休息(工友和劳工权益者莫骂,她当时就是这么一说)。我听了很有触动,在大公司里工作的人往往像笼中拼命奔跑的土拨鼠,我们要绩效更高,我们要规模更大,我们要组织人更多。在这个越来越的语境下,有一些作为人的快乐、从容、思考、慢的权利被剥夺了。除了做一家在空间上不断扩张的机构之外,我们为何不可以做一家屹立百年的街角小店,在时间的纵轴上延续呢?在大即是美的语境下,我们总在说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我们总是从大的框架往下套,我们开口闭口都是普通人听不懂的大词儿、生僻词,用以彰显我们的专业。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甘愿做小呢?专注于小而美,不求规模化,不求扩张,不求一出手就解决整个国家的社会问题,而是认真地做好手边的小事,服务身边的邻里,用心爱自己的员工。看似无声,却代代流传,这样的机构有可能存在吗?
爱在纯山,2007
当梦想闪亮时,自有推动实现的力量。06年初,我以前在证券公司的同事+朋友老和(还记得吗,6000字以前提到过,8秒一沓姐)找到我,说想给我们机构捐点钱。当时宣明会接收国内捐赠的程序非常繁琐,而且要涉及两次汇率损失,老和就敲了退堂鼓。她问我:“捐个钱这么麻烦,那我们自己成立个组织行不行?”我说:“法律上行,实际操作上你找不着主管上级就不行。”老和不信邪,说要试试看。
老和再次联系我是一年以后,她攒了6位捐赠人凑了200万,找到省委统战部做主管单位,用了九个月时间,竟然注册下来了一家基金会,这是全中国第一家挂靠在统战部下的民办基金会,她叫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出生于2006年9月15日,处女座。
07年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纯山教育基金会的初建工作,08年正式入职纯山。近三年的时间里我都一直是个光杆司令,一个人调研、写项目书、筹款、实施、宣传。心里总是惴惴不安的,这种“我说了就算”的滋味其实不好受啊!我找理事长Cindy聊天,抱怨理事会都不管我,Cindy说:“这些发起人都有自己的生意,他们有心发愿做点好事,但他们做公益可不专业。现在台子已经搭好了,要由你唱戏啊。”(领导高段啊!)我立马被忽悠出了感恩的心,低头想想,可不是,我哪里是一个打工者,我是一个创业者。
三年的折腾,纯山从无米之炊逐渐发展到能够筹些钱来做项目,从一发工资就赤字到勒勒裤腰带还有可能再找个帮手了。于是,09年纯山迎来了第二位员工,我赶紧趁机顺水推舟地把自己的工资从2000调整到3200,新员工月薪只有1600。工资这么低,员工二号也是拼了。我们俩一对女汉子,都练就了一身硬功夫,扛着饮水桶一口气上三楼脸不变色心不跳;下乡给乡村图书馆送书,为了省几块钱的车钱,一百本书拿绳子捆起来硬是烧人油送过去。我俩都觉得花自己的钱随便花,花机构的钱必须抠仔细了花,因为那些是别人捐来的善款,每一分都浸着信任、责任和期待,不能辜负。
烧人油最大的弊病在于,人油有时候不可持续。10年,我跟二号去给村小送书的时候,我身负重物摔在山路上,不负众望地断了一条胳膊和一截尾椎。去医院的时候,大夫说要手术,先去交一万,我转身就走了——下海快十年,我的积蓄已经神秘蒸发了,家里还有一个2岁的钞票粉碎机正在嗷嗷待哺。当然,我的胳膊去神奇的老中医那里花了1000块也治好了,可是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我不再给乞讨者钱,因为我觉得我随时就可能是他们的一员;我不愿意参加任何的家庭聚会同学聚会朋友聚会,我不怕别人的嘲弄和鄙夷,我怕我怀疑自己。有一次跟人说起我的工作,那人说:“真伟大啊,拿着佃户的钱,操着主席的心。”还有一次,我一边走一边想着农村妇女在城市务工可能面临的问题,结果不留神跟一位大妈碰上了,还没来得及道歉,就被大妈骂一句:“瓜皮!”五味杂陈,我可不就是个瓜皮(陕西话,傻Ⅹ)。
08年之后,中国公益一路长虹。到12年,国内公益组织从增量、能力水平、涉及领域和资源方面都比十年前,甚至是五年前增加了N个体量。10年还是独臂神尼的我下了个决心,要出去走一走,看看别的组织。这一年我跟Cindy拜访了光华基金会、恩派和其他一些组织,学习了不少先进经验。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原来酒香也怕巷子深,我对Cindy说:“原来中国是个关系社会,在公益行业生存也是要刷脸的。”Cindy老神在在地说:“在全世界都一样!”我们开始制作印刷品,琢磨做网页,得让更多的资源找到我们。同年8月,基金会中心网透明指数首次发布,发布当日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排名37,是前百名里唯一的一家来自西北的基金会。从此,纯山才被人看见。
The End,马上!
写到这里,不止八千,我说写长了没人看,全斌信誓旦旦地说有人看,看到这里的都是真爱啊!
生而为人,一不小心就三十多年,一伸手就要不惑了,突然就懂了老男人的忧桑。听李宗盛的《山丘》,还没能懂得,就快要老了。生命如同一条线,经历是穿在线上的珠子,无论那些珠子美丑大小,都是一条无法拆毁重来的项链。
在公益行业跌跌撞撞了十几年,回首往事,全靠野蛮生长,没有那么多理性的谋划,没有那么多统一的模式,就如一颗萌芽,用尽全力在缝隙里求存。我已经不再相信什么是唯一的标准,不再相信通向远方的只有一条路径,我甚至不再相信成功,反而更加相信失败。如果说成功是人生路上开出的一朵朵的花,那么失败就是那条路,泥泞或者尘土飞扬。
也许,放下了心中奔向成功的明月光,才看得到脚下的方向。
也许,把眼光从世界的救赎中收回来,才看得到身边的人。
甘地说:“爱全世界容易,爱身边的人很难。”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廖瑾2014年成为银杏伙伴,看其它银杏伙伴或公益相关的文章,回复“公益“。

配图:山路归来。
奴隶社会一周年精选文集《女神经过》赞赏版本已售完并全部寄出。再次感谢大家赞赏,辛苦大家久等!书的普通版在4月中旬也会上线当当、亚马逊等网店。
没读经典老文章,你知道你错过了什么吗?发送 m 获得以前的热文目录。有感悟想和大家分享请回复「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