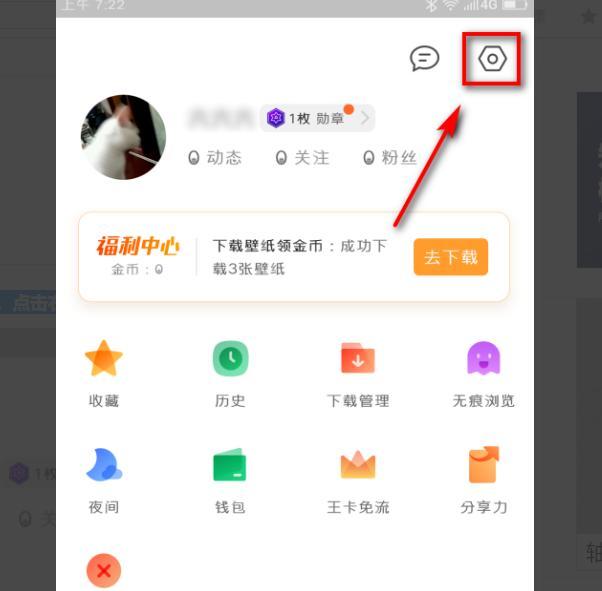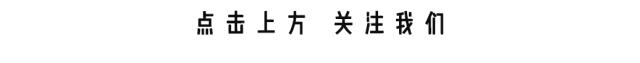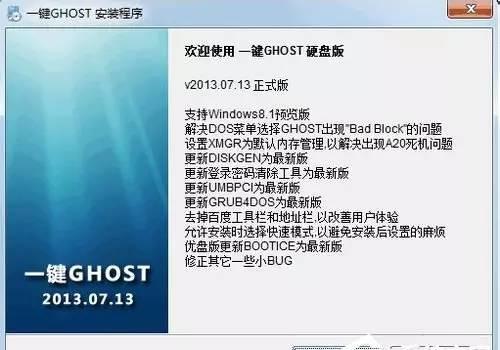我们每个人都因为生活而选择了自己不得不选择的路,我们都曾经反抗过生活的压迫,但大多数人都屈服了,而有些人坚持了下来,或穷困潦倒,或学有所成。接下来的这位20年坚持到现在的农民,值得我们学习。
熊庆华开始上色,他一只手插在裤子口袋,或画,或低头沉思,或转身在筐子里寻找合适的颜料,时而他又后退几步,琢磨整体布局。

熊庆华在自己的画室内 画画。澎湃新闻记者 章文立 图
1976年出生的熊庆华是湖北仙桃永长河村村民,在这个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的村庄里,他差不多是唯一留守的男青年。他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不种地,不工作,不出门,整天躲在家里画画。
在前35年里,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毫无前途可言的人,村民称他“蠢材”。但如今大家开始叫他画家。不仅如此,外界甚至还有人把他称为“中国毕加索”。今年3月26日,他的第三个个人画展又将在北京开幕。
乡村城堡
“喏,就那儿!”没等记者反应过来,司机指着远处一个尖尖的绿屋顶喊道。在一群大同小异又毫无美感的建筑中,它显得鹤立鸡群。
熊庆华的“城堡”,建筑风格在村里显得很特别。 章文立 图
熊庆华主动走上前与记者握手,动作略为拘谨。他身穿靛蓝色薄羽绒服,皮肤黝黑,时常咧嘴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有点“憨”的意味。
熊庆华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心理——并不是说他傲慢冷淡,只是不善表达让他很难轻松融入陌生人的对话,就连与人交流绘画也让他感到窘迫。
他更愿沉溺在自己的世界,因此从小就立下目标,建一个自己的“城堡”。40岁前夕,他在自家菜园子里实现了这个梦想。
“城堡”就是那个“绿屋顶”,这是他的画室:白色的栅栏围着一小栋精致的欧式风格建筑,尖尖的角,朱红色的屋檐,绿色的屋顶,还有喷泉,雕塑 ……大部分建筑元素都无法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找到。只有画室里开垦的几块蔬菜地显示这儿是在农村,青菜叶上还沾着新鲜而潮湿的泥土。
熊庆华每天就窝在这里画画。画室是开放的,阳光透进来倾洒在画布上、地板上、人身上。熊庆华站在画架前,正为一幅新作打草稿。
他有时只是在纸上画了一条线,顺着这条线想,一幅作品便出来了;有时是先想一个主题,再根据主题慢慢想。

熊庆华在画画之余喜欢摄影。澎湃新闻记者 章文立 图
“现在把画画当作什么?从小的梦想可能就是把画画当作一个谋生的手段吧。别人劝我临摹,我就反感,画画要看自己喜欢画什么,怎么能看别人想看什么就画什么呢。”他做出标志性的咧嘴笑表情。
整天沉浸在幻想中的熊庆华,曾幻想过多种成功模式。比如某天写了一段不错的文字,会幻想成为作家;唱了一首不错的歌,会幻想成为歌星。
幻想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而在这多种幻想里,他意识到,唯一能做出成就的就是画画。
这使他感到小有成就,在学校里,他有时故意假装一不小心,把画摊在桌子上,好让同学看到。但倘若发觉哪个同学画画要超过他了,那他是受不了的。
画画也是熊庆华逃避现实世界的一扇窗,“做什么事不成功或者受到挫折的时候我就去画画”。
升入镇中学后,熊庆华住校,内向的他无法适应,成绩下降得厉害。渐渐的,他越来越讨厌学习,经常在课堂上偷偷画画,让别的同学给他打掩护。
同班同学雷才兵那时也喜欢画画,他记得,美术课常被文化课占用,美术老师上课也敷衍起来,没有人教也没有画画的氛围,但熊庆华就是喜欢画,如果美术老师布置一个主题,熊庆华总是画得很好。
他没有经过系统训练,凭借热情和天赋自学,也固执地不愿求教他人。“如果你硬是塞给我一个老师,我就可能不画了。” 他从书上摸索绘画笔法,遇到不懂或者困惑的地方,也绝不愿向会画画的人请教。
他分析自己的脾性深受三哥影响。他的三哥是个农民,却爱好研究历史,读书写诗, 常一边放牛,一边给熊庆华讲历史故事,听多了,熊庆华自认有能力把各种历史事件串联,便瞧不起课堂上教的。
“离开仙桃”
念完初二,熊庆华的文化课成绩已经“惨不忍睹”了,他决定辍学。20世纪90年代,村子里孩子辍学是常见的事。

2012的作品《哥哥的婚礼》
那时,熊庆华才15岁,性格孤僻,不喜欢跟人说话。第二年,雷才兵毕业后骑自行车来找他,他却羞于见同学。
自卑的熊庆华认为画画是一个“高大上”的职业,他渴求从中获得荣光。父亲熊光元当时40岁出头,只有两个孩子,一开始并不强求儿子打工赚钱,他认为画画好歹算“一技之长”,也不错。
那时,熊庆华经常骑两小时的自行车到仙桃市区的图书馆看绘画书。有一个学美术的同学毕业,书不要了,熊庆华就把那人的书都买了,找父亲付了200块钱。拿到书后,他整天就窝在家里研究绘画。
“他内向,你说(话),他也不跟你说。”在父亲熊光元看来,熊庆华一直到现在“搞这个事”,也是他这个性格造成的。
熊元光夫妇都是农民,在绘画方面无能为力,但他们也不强迫他干农活。
“小时候画画,周围人对你更多的是赞赏。一个人有特长,别人总会对你另眼相看。后来慢慢长大,又不去做事,别人好像感觉你这个人一生会废掉。”熊庆华已经慢慢感受到周围人态度的变化。
那段时间,迈克尔·杰克逊刚开始流行,他买了一盘磁带,每天用收音机放杰克逊的歌,边听边画画。“邻居都听得吵死了,都说你怎么天天听一些哭啊吵架的东西。”
村里和他同龄的孩子,基本都出去打工了。冷嘲热讽越来越多,父亲熊光元有时也忍不住说:“你(干吗)非要搞这个事,你那些读美院的同学也没搞成功。”
同样喜欢画画的同学雷才兵走上了另一条路。他初三参加了美术培训班,考上了中等师范学校美术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镇上当老师,当时镇上已经有了美术教师,便派他教数学。
教书头几年,雷才兵还随身带个速写本,闲暇之余画些东西。后来有了其他的兴趣爱好,开始打篮球、乒乓球,慢慢就不画了。
非议在熊庆华结婚后达到顶峰。1998年,经人介绍,他认识另一个村庄的女孩付爱娇,她比他小一岁,认识10个月后,两人结婚了。
“那是到了一个年纪吧,可能要完成父母的期待,或者任何一个年轻人要完成的任务。”他总结自己婚姻的起源。至于爱情,他害羞地笑起来,“哈哈哈……这怎么说”。
他称呼妻子是“最亲的人”,画画烦躁的时候可能只对“认为最亲的人”发火。

熊庆华在房间墙壁上给妻子画的画像
付爱娇起初对丈夫“整天画画”的事一无所知,知道后一度对他崇拜不已。两人婚后育有一子,但随着孩子长大,付爱娇越来越希望丈夫可以出去打工挣钱,熊庆华依然不愿意。
小学四年级就辍学的付爱娇没有什么技能。2003年,她决定独自去深圳打工。妻子离开后,经不住邻里家人的舆论压力,熊庆华决定外出打工,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仙桃。
他去了一家工厂流水线,负责清理手表外壳上的毛料。他一天清理200多个手表,而他身边一个老头一天可以做几千个。熊庆华觉得自尊受挫,三天后,招呼也不打就走了。
2006年,熊庆华又做了第二次尝试。他得知深圳有个大芬村,很多人在那里做画工。
大芬村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有60多家规模相对较大的油画经营公司,1200多家画廊、工作室以及绘画材料门店。
熊庆华打算去找个画画的活儿,他把作品带去了,结果画廊老板提出各种质疑,说“你都画了些什么东西啊,你的基础根本不行啊”。
一直梦想成为最伟大画家的熊庆华,心里落差非常大,“想死的心都有”:“努力了这么多年,一下子就被人全部抹杀了。”
但过了几天之后,他又恢复了“打不倒的小强”本色:“你瞧不起我,我偏要在这一行做出成绩来。”
那天晚上,熊庆华去厂里接妻子回租住的小屋。路上,妻子一直劝他安安心心找一份工作,“坚持一年,我们一起回去。”这是付爱娇当时最低的要求。
熊庆华却突然烦躁起来,“我永远不会在工厂做事!”他一甩妻子的手,闷着头就往前走。通往出租屋的路黑黢黢的,付爱娇喊住他,说:“你要往哪里去?”熊庆华心里也觉得很好笑:“是的,我能往哪里去呢?”
“独狼”
最困难的时期,有邻居劝诫付爱娇夺掉他的画笔,偷掉他的画具。但后来,妻子也心灰意冷了。“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怀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情回到村里后,熊庆华觉得一生画画如果没什么名堂也就没什么名堂,大不了种田嘛,反正在农村也不会饿死。
村子里早已闲话四起。“各种各样难听的话都有,什么最没有用的人啊,蠢才啊……就连父母也时不时影射自己为蠢材。”

2015年的作品《扬谷》
“蠢材”是当地对一个人最低的评价,逆反心理很重的熊庆华觉得,“他们越说,我就偏要向那个方向走。”
他每天带着儿子一起画画,两人一块在墙上涂鸦。儿子把下面的墙涂完了,他又拿着梯子爬到房顶上画,墙壁全部画满了后,他索性把墙都粉刷了重新画。
永长河村主要种植水稻,外加小麦和油菜。家里的收入完全靠着妻子打工,父母种地、养鱼塘。付爱娇在电子厂打工,每个月工资不到1000块,每年回家,她把钱一股脑都给丈夫用。
“我从父母那里要不到钱画画,只能跟老婆要点,自己再打点零工,摸摸虾。”为了买笔和纸,熊庆华去田沟里摸泥鳅,挖鳝鱼。
但他做这些事都坚持不了十天。“做十天之后我就各种怨言,找各种理由不干了,你把钱给我吧。钱一到手,我就去买绘画材料,没钱了我又去给人做事。”
他不是一个好的庄稼汉,农活基本都干不好。也插过秧,但插得既慢也不规范。送牛奶是他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2007年,他每天早上四点多起床给村民送牛奶,一直送到七点半左右。这不会影响他画画,也买得起油画材料了。他一个月大概赚900块钱,坚持了一两年。
熊庆华的创作灵感大都源于农村生活,但他的画笔落到画布上有种幽默的天马行空。比如,几个孩童踩到西瓜皮摔倒了,他画里的西瓜皮碎片漫天飞舞,孩子们手舞足蹈,动作夸张。
坐在门口闲聊的邻居议论着他的画:“我们老看他画,就搞不清楚什么名堂”;“太深奥了也不懂,我们只能有时候看得懂”;“有的是打鱼,有的是玩耍……”
他从不在乎村里人的眼光。“我一直认为,做艺术就是纯粹自我,过多地在乎别人的眼光是做不好艺术的。”他形容自己从小就像只独狼,喜欢一个人到处跑,玩耍也不合群。
“他认为我们不懂,跟他谈不到一块。”父亲熊光元一边在磨刀石上磨着镰刀,一边嘟囔说:“我们要是发表一点看法,他就说你不晓得!”
妻子付爱娇身形微胖,有张温和的圆脸。她今年39岁,普通话带些方言口音,回答问题时总是羞涩地笑起来。有时无聊,付爱娇也会来看看丈夫画画。她并不都能看懂,但也不会去问,担心丈夫说她“操冤枉心”。
结婚之初,熊庆华曾跟妻子交流过几次画画,但感觉说的不合自己胃口。“她指出应该怎么画、应该画什么后,我就不想跟她说了。”

2010年的作品《老鹰捉小鸡》
大多时候,付爱娇扮演的是一个勤恳而任劳任怨的主妇角色。她打工赚钱,照顾丈夫和儿子的起居,几乎从不参与熊庆华的创作。
画家
2003年,在当了8年乡镇中学教师后,26岁的雷才兵嫌工资太低,地方太小,辞职去了深圳打工。
在深圳的那些年,雷才兵没有见过熊庆华,但他偶尔会听说,熊庆华还在家里画画,赚不到钱,很孤僻。“当时觉得他这个人很固执,看不到未来的情况下做这么久。”
2009年,两人偶遇。雷才兵记得,当时熊庆华完全是一幅农民打扮,整个人甚至比一般的农民还要沉默,“他很内向,孤僻,不自信。”
雷才兵问他在干嘛?“我说我在画画,就觉得很丑(丢人)。”熊庆华很不好意思。此时的熊庆华正处于人生中很绝望的时刻,他再次面临着是否要出去打工的抉择。
雷才兵想看看他这些年都画了些什么。一进他家,就看到大门上熊庆华画的门神,二楼有个房间是熊庆华的画室,天花顶上、墙壁上、木床上、画架上都是他的画。他没钱买画框画布,只得自己用木头做画框,蒙上白布就画,有时布不好,破了,他就随随便便作为装饰订在墙上。
雷才兵惊奇不已,拿着相机到处拍。他喜欢这些画,在他看来熊庆华的画贴近现实,“但不是纯写实,而是经过了提炼、夸张”。
之后,雷才兵在一些论坛上开了帖子,陆续上传熊庆华的作品。过了两三个月,网上反响很好。
过去从未接触过网络的熊庆华,世界像是被打开了。他原本只是期待雷才兵能把他的画介绍给某个老板,给自己找份工作。但没想到网络上有这么多人喜欢自己的画,雷才兵告诉他,每天要顶一下帖子,帖子才不会沉,让他再发点画过来。
熊庆华像是看到了希望,他加紧创作。为了拍画传给雷才兵,他买了人生第一台卡片相机。周围的邻居都说他疯了,花1000块钱买这个东西。
“当时最大的希望是一幅画卖两三百块钱,像大芬村一样。”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画会有人买,甚至也不知道如何定价,他去问雷才兵,最终以1000元一幅卖了5幅画。
“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邻居说,啊,一幅画一千啊,谁这么蠢啊。”他回忆时,又忍不住咧开嘴笑了。

2013年作品《渔民》
熊庆华当时不善言辞,普通话又不好,沟通很困难,最终还是熊才兵帮他谈下这笔交易。由于画框很大,邮政不让寄,镇上又没有快递,熊庆华只能把五幅画堆起来背到仙桃市区物流处寄送。
卖了第一批画之后,他给自己买了台电脑,开始自己发帖,卖画。网上的作品吸引了他后来的策展人郭宇宽。
郭宇宽对那些画“过目不忘”,从北京一路南下,寻到熊庆华家。“不像北京宋庄,那地方没有一点艺术气息。”郭宇宽回忆说。
熊庆华从床底拉出来好几幅画给他看。后来,郭宇宽把身上的2万块钱都给他了,以5000元一幅的价格买了几幅。他告诉熊庆华,以后每个月买他一幅画,并且给他5000元工资。
2014年,郭宇宽开始做画廊,要给熊庆华办展。2015年1月和2016年7月,熊庆华先后两次在北京举办了个人画展。
郭宇宽说,最早一些艺术评论界的人不认可他,美院的画家说他画的一点都不好。“熊庆华是野路子杀出来的,美院的人学了一辈子基本功,所以抵触比较大。”
画家黄志琼觉得,熊庆华的画的确是有些想象力,带点诙谐、调侃。但他认为熊庆华的画属于农村风俗画类型,不是艺术作品,不能进入当下的艺术语境。“他的画不少人很喜欢,是因为很容易明白作品里的故事”
郭宇宽认为,熊庆华的天性里有着诙谐乐天的部分,“在穷成这样的一个地方创作,他不是愁眉苦脸的,是自得其乐的。”
对于一直习惯独自琢磨的熊庆华来说,艺术上的规范需要遵从,不能完全打破,“比如说,构图上怎样保持均衡,色彩上如何调配。”
但他同样坚持,画画是一种出于人本能的东西,过于强调基本功这套思想是过时的。“像罗忠义,他这么高深的美术工底都不做写实,你还强迫后来的人再去学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他到外面也很少跟人交流绘画,“基本上都是客套话,他们的某些观点我也不会赞同。”
“熊熊火”
8年来,熊庆华的画早已从单幅一千元涨到六七万元。他不再是村里“没有用的人”,而是人尽皆知的画家。他现在有了一个学生,是村里喜欢画画的孩子。
雷才兵感觉熊庆华如今比过去开朗自信很多。原来基本不跟外人接触的他,今年春节还去参加了初中同学聚会。采访期间,熊庆华的几个初中同学来看他,还有同样爱好摄影的朋友专门从市区开车来拜访他。
但如果没有朋友来,他也不觉得孤单。几十年来,他早已习惯了一个人。成名后,除了给自己建了个“城堡”外,他的生活基本与之前一样,他不买车,不买房,也依然不爱出门。

2014年作品《驮》
互联网为他解决了生活和创作材料的问题。过去没有网络,他经常坐三个小时的公交车去武汉买绘画材料和书。“那时画布很重,颜料也很重,我用一个蛇皮袋装满,然后扛回来。”
现在,需要什么材料,他都从网上买,画画累了,就去做些手工,修理一下喷泉。画室的建筑都是他自己设计建造的,画室外面挂着“涤渡”两个大字,是熊庆华起的名字,表示“在河边画画”。
他对一切视觉传达的东西感兴趣,如今最大的支出是摄影,买了各种顶级相机和镜头。去年春节,他买了无人机玩航拍,想从天空看看自己生活的地方。
郭宇宽曾问熊庆华要不要来北京发展,熊庆华说还是喜欢乡村的环境,他在城市里很迷惘,走在街上都会迷路。虽然他并不喜欢村里的人,也不喜欢他们讨论的话题,但时间久了,他又会很想见那些村人。
“这个地方是我创作的根,离开这个地方,感觉也不想画画了。”他缓慢而又慵懒地说着,“只有住在这里心才能静下来,才能天天想如何画画,怎么画。”
鸟在林子里叫着,叽叽喳喳,农村的妇女们在“城堡”外头聊天,也是叽叽喳喳。当熊庆华沉浸在画室里时,付爱娇带孩子,忙家务,或者跟一群村民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晒太阳,他们闲聊,话题无非孩子、麻将这些琐事。熊庆华从不参与,“跟他们谈不拢。”
付爱娇不再出去打工,人们羡慕她,总算熬出了头。过去独自在外打工时,有时在路上看到别的夫妻或情侣,付爱娇常常失落。但熊庆华没有对妻子感到过内疚,“因为我要画画,要是内疚,肯定没法画画了。”
付爱娇感到丈夫不够关心她,她说着说着就眼里泛泪。今年情人节,她说,过情人节了啊。熊庆华说,情人节是给情人买东西,又不是给老婆买东西。
熊庆华唯一为妻子做过的事还是画画。在旧屋二楼的卧室里,床头墙壁上有一张妻子穿着婚纱的巨幅画像,这是2004年、2005年妻子在外打工时,熊庆华陆陆续续画完的。“因为我们结婚时没有拍婚纱照,她就老要我补拍,我一直不肯。我觉得结婚都好几年了,没必要浪费钱拍。”于是他就亲自在墙上画妻子的画像。

熊庆华的摄影作品
画画已经融入到他的生命之中,无时无刻不受它影响。画得很有感觉,心情就会很好;画得很糟糕,心情也会很糟糕;如果哪天不画又觉得很失落。
有时画画烦躁,跟他说话都会被骂。要是妻子对骂,他就暴跳如雷了。妻子被吼了后,就一个人躲在床上偷偷哭。
这时,画画再次成为熊庆华逃避现实的出口。他从来不去哄妻子,“我被她弄得心情烦躁,就要靠画画去调节,直到自己心情好一点。”
对他来说,画画一直都高于一切,他时常感叹画画的时间还不够,“每天画一下一天就过去了。”
他的朋友郑刚打扮整齐入时,倚着池边的栏杆情不自禁地说:“这是他的庄园,一直不断在建设,去年来的时候还没有栅栏。”
原本,郑刚想叫熊庆华一起去武汉拍照,但熊庆华不去。他喜欢自己安排事情,不希望画画节奏被打乱。
画室里到处都是画,刚完成的、未完成的,油迹未干,他提醒我们不要弄到身上。随后,他展示了柜子里这两个月的作品,将近10幅。
他从2008年真正开始创作,一年创作5-10幅画。2010年后,他开始要求自己一个月保持创作4幅画的频率。他的目标是一生画2000幅油画。
前几天,一个70多岁的老人去拜访他,自我介绍说画画一生,没有成功。“如果我不被认可,可能跟他一样。”熊庆华时常有危机感,一想到万一哪天自己的画别人不喜欢了,就觉得恐惧。
他现在每天早上7点起床,8点多吃饭,大概9点开始画画,一画就画到晚上10点。他觉得自己在绘画方面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想创造自己的绘画风格,“辨识度非常高,让别人一看就知道,啊,这是熊庆华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