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中说: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谢邀。
《庄子》中说: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我们今天还用得很多,大多是用来指代对一件事情,或者对一个人完全失望,以至于进入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状态。
就是随便你怎么样吧,反正已经与我无关了。
现在对于“心死”的解释,基本上就是认为个人完全失去了对目标的兴趣和动力,心如古井,不起波澜,有如一潭死水。
现代大众理解其实很简单,还有什么比心死更让人悲伤的事情吗?
没有了。所以这是形容悲哀、悲伤到了极致。

不过这是口头理解,实际上官方的解释并非如此。
现代意义是:指最悲哀的事,莫过于思想顽钝,麻木不仁。
也就是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情沮丧、意志消沉到不能自拔。
心死:指心如死灰的灰烬,思想顽钝,对周围的事无动于衷。
这里的解释就比单独的情爱之伤要广阔多了。我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习以为常,我们对世风日下的冷漠旁观,基本上都可以划入“心死”的范围,这种行为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悲哀——瞬间整个认识就上了一个层面,远比在感情中的绝望更加有高度。
很明显这是对文言文的世俗化,因为我们上溯根源,就会发现庄子的本意确实要高邈得多——原本是基于道家生死观的认识,而并非浅层情感希望、失望之中的变化。
“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出自《庄子》外篇《田子方》。

我们要真正理解这句话,首先得搞清楚庄子的生死观。
老庄道家思维中,老子探讨“道”和“德”的含义,涉及的是宇宙万事万物的起始、衍变及规律,提出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相处的“至善”原则。
老子的思想是一种底层的哲学思维。
庄子则是以老子人与自然的思维为起点,更多地关注人的生死,以及在他的生死观之下的人类价值体现。
庄子认为生死本一,并没有区别,生死的区别只是存在的状态不同而已。不仅生死如此,万物也平等如一,此为“齐物论”。
在庄子看来,一个人是由精神和肉体两种元素组成。咱们用写文章打比方,即内容和形式。而作为形式的肉体,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为其他的形式,比如风、气,这只是“道”的形式转换,并不代表着“道”的消失。

而这种转换,在平常人看来,就是死。
为什么他老婆死了,庄子不但不悲哀,还“鼓盆而歌”?因为他认为夫人不过是转换成为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罢了。他没有死的概念,自然没有生离死别的悲哀——这种思维被用来安慰活着的人,实在是属于大众对死亡无可奈何地接受。
因为无可奈何,所以无法不悲伤,只能减弱而已,而庄子是真的从内心就没有悲伤,表现看起来相似,其实对事物内核的理解完全不同。
这种肉体消失转化,就是形式的转变,为了写出来让后学看懂,庄子使用了“人死”这个词。

那么“心死”,自然是指精神方面的死亡、丧失。比如失去上进心、失去思考能力,失去辨别能力,也就是说关于思想的任何活动都停滞了。
用现代医学的例子来说,“心死”是“脑死亡”,而“人死”是器官衰竭死亡。
那么是“脑死亡”可怕,还是人体功能丧失可怕呢?
都一样可怕。
但是人体功能丧失有全部和部分,部分者缺手缺脚,那可比脑死亡要好多了,甚至还可以正常生活;严重的全身瘫痪,可只要没有“脑死亡”,就有活下去的希望,有求生意志——因为精神还在,因为心没死。
这样简单地类比,是不是就可以说明人最大的悲哀就是“心死”,而“人死”要稍微次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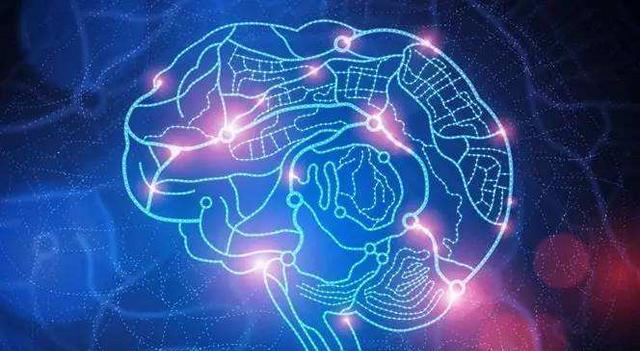
就好像脑死亡、植物人(类脑死,但是有可能复原)、全身瘫痪,三种非常可怕的境况让人选,如果有得选又必须选,只怕全身瘫痪是最能让人接受的一种选择吧。
有人说,我宁可死,也不要瘫痪——这个其实未必能以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旁观分析得出的结论来表态的。
庄子认为肉体和精神是可以分离的,能够到达那个境界,就是“逍遥游”了。精神不用凭借任何力量,自由自在地在宇宙中畅游。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庄子自身也并没有达到,但是他提出“坐忘”、“忘我”等方法,希望能借“呆若木鸡”达到这种境界。

庄子追求“大用”,即心的存在和延续,而“无用”就是肉体的无用,所以“无用”才能致“大用”。歪脖子树因为不成材,得以保存,其实不过也就是说借助形式的“无用”,保住了心的“大用”。
所以这句话翻成大白话,其实就是说:“停止思考的人苟活于世,比肉体死亡的人更加可怜”。
即使在今天,同样有其正面意义。
“肉身无法百年康健,精神可以万世传颂”,这种对高于肉体的精神追求的理论灯塔,对人类的社会活动意义、生命价值追寻也有着积极正面的指导作用。
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如果纯粹只是用来分手,未免太小家子气了些。

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人心什么意思?
1.这句话字面的意思是:我从来不怕从最坏最心存恶意的方面去推测中国人。
这句话出自《纪念刘和珍君》,原文是这样的: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表示尽管自己惯于冷眼看待军阀政府的文过饰非,从最坏最恶毒的方面去推测他们可能的做法,仍然料不到他们竟然凶残到超出自己的想象。
“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卑鄙无耻、比这更凶残的吗?下文“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直接表达了鲁迅先生对如此文治武功的段祺瑞执政府的强烈的愤慨,已经对国民性丑恶面的深沉的反思。
2.字面意思是指我从来不怕从最坏最心存恶意的想法去推测中国人。结合当上社会背景来理解是指当时的社会风气败坏,军阀政府文过饰非,鲁迅已经想到了政府的可恶与卑鄙,可仍然料不到他们竟然凶残到更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鲁迅对政府迫害刘和珍君的抗议和谴责。
此句出自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原文是这样的:“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
刘和珍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年仅22岁。鲁迅先生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亲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殒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