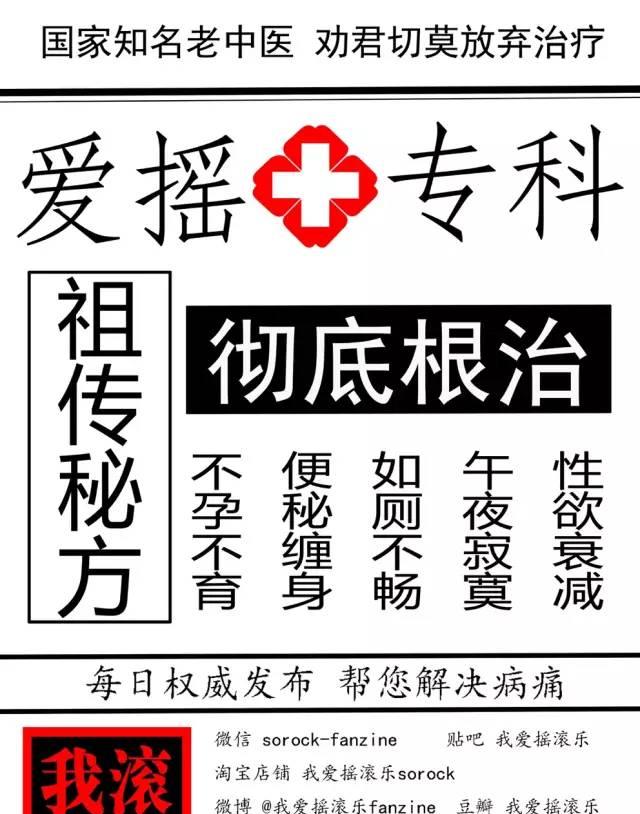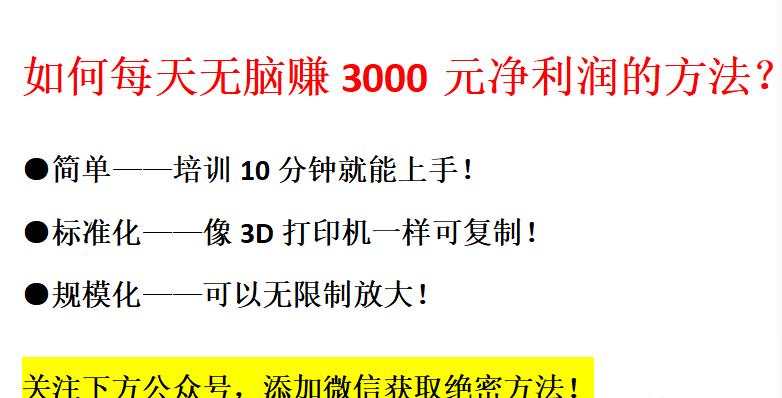by : 颜峻
新版附记:
这篇文章最早写于2007年,在《音乐时空》连载。后来经过几次修订。最后一次,是2015年印刷《野兽档案》的时候。现在你看到的,就是这个版本。之前有一些非授权的发布,应该都不是,且有错漏。
《野兽档案》是对我涉及中国摇滚乐的文章的集结,只印了两本。不过稍早一点,已经做了 PDF 版,放在撒把芥末和我个人网站上,供免费下载。
经过这么久,很多事情又有了发展,或者有了新的理解。最大的变化是我自己,今天我是不会再写这种文章了,题目太大,写多了,会觉得自己也大。
文章里仍有不少错漏,有些是井蛙之见,或者含混的理解。比如说,“前卫”和“先锋”这两个貌似不一样,或者说貌似一样的概念。现在也没法一一去改了。人生总是充满遗憾。不过,相信很快会有人另外写更好的文章,或者书。
但哪样东西没有经过翻译呢?连所谓的传统,不是也经过了时间的翻译么?只不过有的人是在翻译中游泳,有的人是在挣扎,或者已经陷入永恒的宁静。
谢谢大家!
颜峻。2018.6
一、词
中国电子乐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题目,至少,这是一个几乎无法界定的名词。因为技术和文化的差异,这个词在使用中脱离了英文的原意,和中国当代的许多词一样,变得含混、交错、游移,不同人的使用,含义根本不同。所以我们先来谈论中国人理解的“电子乐”。
在大众媒体上,电子乐是流行乐的一个分支,或许有歌词和传统歌曲结构,比如“与非门”、“龙宽九段”,或者随便哪个歌手的“电子时尚新作”。看在年轻媒体人的份上,现在也包括了土产的山水唱片、打口的Warp,也就是圈里人说的Electronica;以及四川云南文艺青年常说的“民电”、“电爵”。最后,顺便的,也捎带上了从DJ Sasha到东北粗口迪曲在内的所有电子舞曲;当然,如果是DJ在媒体上说话,那么,“电子”、“电音”就等于电子设备制作出来的节奏性音乐,尤其是4/4拍舞曲。
但也不对……在“圈里”,也就是电子、摇滚、另类这个比较新鲜的音乐圈,从1998年以后的《通俗歌曲》到今天的《音乐时空》的读者圈,电子乐也不等于Electronica;准确地说,在西方流行乐的分类里,Electronica(较独立的流行类电子音乐,范围最广)、Ambient(无节拍或弱化节拍的氛围音乐)、IDM(“聪明舞曲”,复杂多变的节拍游戏)、Drum ‘n’ Bass(快速的节拍和低音,听起来噼里啪啦)、8 bit(又称Chiptune,旧电脑和任天堂游戏机的复古舞曲)、Electro(低音丰富)、Chill Out(起源于跳舞累了需要放松)往往是分开用的,但在我们这里,要算在一起,统称电子乐。有时候,我们还要加上工业音乐(准确地说,是工业音乐在1980年代中期的电子分支)、Electroclash和电子舞曲。这其实是因为在1990年代,新青年刚从摇滚乐的兴奋中消停下来,所有带机器味道的就都是电子乐,就像所有白种人的脸看起来都一样……这样深究下去,可以考察到中国电子乐的一个文化脉络,我们稍后再跟它磕……
音乐圈当然不只一个,而且彼此间严重隔绝。在学院圈里,“电子乐”就是一个相当不严谨的说法,因为Electronica还不配称作音乐,世界上只有古典乐、民族乐、流行乐和“电子音乐”,所以学报上一般不说“电子乐”。那么什么是“电子音乐”呢?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电子音乐中心,“电子音乐”是指法国具象音乐(Musique Concrète)传统下的电子原音音乐(Electroacoustic Music),因为这个中心的老板,是法国海龟。
基本上,具象音乐和电子原音音乐,是强调声音的源头和处理方法:源头是原声(acoustic)的,乐器、说话、流水之类;处理是调变(modulation),是把这些声音电子化,变成别的,并组合起来。学院派说的“电脑音乐”,是强调电脑程序的偶然、互动、算法以及新的控制界面的研发;但因为Electroacoustic Music已经是主流,又通常要用复杂的电脑算法、比较新的控制界面,所以它也和“Computer music”算在一起。在中国,也有不少人坚持用“计算机音乐”,而不是“电脑音乐”,旨在强调这种音乐的“计算”(computing)性质。但对某些坚持1950年代传统的电子原音作曲家来说,他们和电脑没关系,因为法国人发明电子原音,是靠磁带[ii]的剪切、拼贴、倒放、变速;那些只玩磁带的,就是磁带音乐家了。
在中央音乐学院门口的天天音乐书店,可以买到“电脑音乐”的教学VCD。这种说法,相当简便、大众,一听就明白——用到电脑的流行音乐,就是电脑音乐;但和国际学院派所说的电脑音乐无关。这种教学资料的主讲,有教授,也有自学成材的实践派高手;讲的是Cakewalk[iii],而不是MAX/msp或者Protools,美学也和电子音乐无关。从事这种替代性音乐的人,其实,何止百倍于学院和文艺青年圈。而这种音乐,说白了就是90年代的“MIDI音乐”,也就是用软件、合成器和其他机器,取代庞大的真乐器编制,主要目标是节约人力资源,次要目标是突出假乐器的陌生效果。现在电脑越来越强大,很多机器都被软件模仿或取代,连合成器也可以是软件,所以“电脑音乐”这个词就取代了“MIDI音乐”。在人类历史上,假的东西往往比真实的要有价值,因为造假意味着科技和进步。而“MIDI”、“电脑”这些词,就像“SOD”、“纳米”、“数字”一样,闪烁着新世界的神奇光环——这都是些形容词。
姚大钧曾经说:“目前国人所称的MIDI音乐只是‘合成器流行音乐’,绝非电脑音乐!!。你要是在中文网路上或任何中文书刊文章里(‘前卫音乐网’上的除外)看到‘电脑音乐’四个大字,就知道它实际上是指‘合成器流行音乐’,跟音乐界所说的真正的电脑音乐无关。”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得到改观,因为年轻人看了他的文章,觉得有道理,也就开始讲道理了。但大多数人有他们自己的道理,这事老百姓说了算;何况,那些在本土流行音乐产业中勤劳耕作的人,不会因为别人的道理,而放弃自己的习惯。
二,文化
从对词汇的使用,可以看到人们的背景和态度。中国电子乐因此就有了不同的来路。
从文化上划分:前边说到的,大致有草莽、商业和学院这三个势力范围。
二点一:
草莽,又称街头,或者新青年,再或者文艺青年。出于兴趣而创造、聆听、消费音乐,曾经在文化沙漠中拼死攫取新的音乐资讯,即使后来变成商业新贵,也保持了对“新”和“品位”的追求。比如张亚东。这个群体变化很快,信息更迭、理论吸收的吞吐量也大,从前的盲目尝试,现在已经分化为不同流派;通过自学,草莽学习学院派技术的速度也相当快,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整个中国学院体系。至于商业,当然,草莽是商业的活力源头,也是商业音乐中时尚神话的始作俑者,张亚东大概是最好的例子。
这个阵营基本和国外的非学院电子乐对接。1980年代以前,电子只是流行乐的一种手段,最多是一个分支,例如德国摇滚(Krautrock)和太空摇滚(Space rock),穆格合成器流行以后,MoogPop也成为一个流派。1980年代,迪斯科发展到House和Techno,合成器流行乐发展到电子流行乐,Hip-Hop兴起,重复节拍和采样变成当代音乐的重要元素,随后就有了我们熟悉的各种新锐电子乐风潮。这个脉络和学院的关系并不很大,因为学院需要庞大的财力和社会资源支撑,草莽却可以用越来越廉价、越来越强大的机器来工作。没有学院的沉重理论和师承,以音乐为乐,以硬件为创作条件,以身体感官为出发点,这样就有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调变美学的小传统。
中国的草莽也是这样,得到什么设备,就创作什么音乐:合成器在中国流行起来,已经不是带振荡器的传统合成器,而是预制音色的懒人机器,因此音乐人并不了解声音的产生过程,也不需要自己设计声音,而是拿它当高级电子琴来用。听到西方1990年代的电子乐以后,人们找来音序器和采样器,制作以节奏为主的电子乐。在布莱安·伊诺和ambient也传入之后,就变成用弱化了节拍的电子乐来超越有节拍的电子乐,这时候,电脑已经成为主要的工具。再往后,软件囊括了所有硬件的功能,西方电子乐的制作传统被直接跳过,人们直接学习作品,而不是工具本身蕴涵的文化。
二点二:
商业,不是说发了财才是商业,而是以发财(或混口饭吃)为主要目标,比品位更看重敬业,比自我更看重客户,这叫商业。这个势力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这些人是老百姓派来的。这个群体对词汇的滥用,和他们对技术的追求是相关联的,因为老百姓是现实主义者,MIDI也罢,电脑也罢,Drum ‘n’ Bass也罢,Techno也罢,真正让外来文化本土化的是他们。当然,商业力量少不了学院的加盟,这是政治资源、技术资源和商业资源合谋的事业,很多学院人士投奔,或者兼跨商业领域,这样就产生了大量针对主流消费者的合成器流行乐、新世纪音乐、影视配乐。商业的创造性在于和市场的互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全民审美停留在简单旋律和简单感官反应上,电子乐美学对大众来说,显然超前太多。因此中国最庞大的“电子乐”制作群体,只是在利用电子乐的技术,来缓慢刷新陈旧的音乐审美,换汤不换药就是了。
二点三:
学院,其实应该说“官方”[iv],否则外国人会听不懂,因为在很多国家,比如瑞典,学院派是和地下息息相关的;在另一些国家,学院意味着新发明和纯音乐。但中国的学院,不是在搞音乐,而是在搞政治。所以这样的音乐必须有门派(比如说,是法系还是美系,本地的师承又是谁),有帮派(比如说,各国的学院、学会利益集团),有任务(比如说,要为春晚做音乐,要为运动会写赞歌,还要帮政府塑造科技和人文的双重神话),同时还要能向媒体和官员解释自己在干嘛(比如说,要有主题,歌颂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宏扬传统、传播友谊、探讨民族文化和当代哲学,并唾弃商业流行乐)。
二点四:
教育体制的变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大师班、工作坊的流行,让年轻人有更多机会学习,学院外的电子音乐/电子艺术中心既分担了教育、研发功能,也把传统学院派和街头草莽放到了同一平台上,像Luc Ferrari这样的活跃分子,已经列入了年轻人、反叛者的偶像名单。在Sub Rosa等独立厂牌的发掘下,从达达到激浪派,从各国早期磁带音乐实验,到早期噪音探索,一个重新梳理电子乐、噪音和声音艺术历史脉络的趋势,在最近10年变得明显起来。
这些变化的前因和后果,在中国都是几乎不存在的。而且,西方早期学院外叛逆所建立的传统,在中国也并不存在,1960年代,作家威廉·巴勒斯用磁带玩拼贴,对1980、1990年代的拼贴实验影响很大。很多人童年就接触磁带机,或者身处二手设备市场发达的国家,今天的地下/实验音乐中使用磁带机,也非常普遍,像日本地下摇滚/噪音艺人山冢爱,就利用磁带机制造迷幻效果;澳大利亚的The Loop Orchestra,用磁带机做为惟一乐器,已经有20多年;美国新极简音乐家威廉·巴辛斯基也将磁带机的loop功能发扬到了极致。这是学院外的“具象音乐”。中国的学院外电子音乐家,对声音的产生、加工缺乏认识,属于历史缺陷。如果说文化的形成,和科技、产品的应用有直接联系,那么,磁带机和黑胶唱机在大众生活中的缺席,在中国当代音乐的先天营养谱系上,是莫大的遗憾。
三点一,背景·大众
所以,要迁就中国特色,这篇文章谈论的,不光是电子乐,也要包括被认为是电子乐的一切。这关系到中国人赋予了“电子”什么意义,就像台湾人把“数位”[v]当作菩萨供起来一样,“电子”首先是新时代的象征。
早在1978年,导演严寄洲就从上海音乐学院的仓库里找到了中国惟一的一台日产合成器,请陈传熙为电影《猎字99号》创作了配乐,这是中国电影里最早出现电子合成声音。此后贺锡德为《潜海姑娘》创作了合成器拟音和配乐,同年的《黑三角》也请王酩用电子乐做配乐。1979年,王酩为电影《小花》做插曲,又把民乐、管弦乐和电子琴结合起来。但最早把电子乐(广义的)带来的,是法国人让-米歇尔·雅尔,用合成器演奏简化了的、娱乐化的古典音乐,按严格的分法,应该算合成器流行乐而不是电子乐。当然他老师很正宗,是具象音乐之父皮埃尔·谢弗。1981年他在北京和上海公演,年轻人为之震惊。那种缥缈的音色、庞大的结构、新奇的声光系统、闻所未闻的技术,和那个充满了朝气和希望的时代相吻合,并且,这套语法一直持续到80年代尾声,逐步从宏大抒情降落到身体叙事,最后,和《摇滚青年》最后的迪斯科浪漫主义一起消亡。
雅尔的影响,马上被国营唱片公司继承下去。1982年到1983年,和瑜伽老师张惠兰合作的朝阳电子乐队,在中国发表了三张专辑,成为第二个成功的电子乐(严格地说,是new age音乐)事件。不堪生活之重的中国人,被他们放松下来,享受起了冥想中的自然、灵性和未来。现在一说到80年代电子乐,人们都会想起这个乐队,并丝毫没有意识到,那不过是一个瑜伽老师(乐队创建者柏忠言)配合身体训练而创作的音乐,在唱片店归类为健康音乐(Health Music)。
然后是本土资源的决定性跟进。上海的屠巴海、浦琦璋开始用电子琴演奏,这样就为“通俗歌曲”贡献了新奇的音色,从苏联大妈沉重的铜管,跃向了沙滩上慢动作奔跑的西方少女。仅仅用来放松、不承载宣教功能的“轻音乐”也随之深入人心。1984年,蒲琪璋用雅马哈FX-50电子琴演奏的《渔舟唱晚》被央视选用,这就是今天还在用的“天气预报”配乐。1983年,侯德健带来了合成器,郭峰、黑子、毕晓世等人就从他那里开始学习新的编曲方法。如果说电子琴只是改变了音色,那么合成器就可能导致新语法的发现。1984年,广州的何文彪改写了历史,他用Roland合成器演奏的《巴比伦》等作品由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发行,那些密集的、快速的、太空的声音令人振奋,节奏和装饰音甚至超过了旋律的比重,这意味着,他已经到达传统流行乐和电子乐的中间地带。
何文彪很快被推广,并对迪斯科文化产生了莫大的影响——80年代中期的国产迪斯科音乐,大多数是从名曲改编而来的合成器作品,对重音并不强调。1987年,《八七狂热》(广州)、迈克尔·杰克逊的《真棒》(美国)、《荷东》(香港)以及随后的《猛士》系列,开始加大感官刺激,提供性暗示,浪漫主义终于从太空降落到本土街头,年轻人也不再因为聚众跳舞而被捕。后来的霹雳舞热潮,进一步综合了流行音乐、流氓文化、外来青少年亚文化和本土青少年自觉意识,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噼里啪啦、连绵不绝的合成器音乐,和魔术般的舞步一起,让我们超越了贫瘠的现实,并且物以类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一切,和电子音色、“电子”一词所隐含的西方、发达、物质主义是一致的,电子,是想象另一个世界的中介。
三点二,背景·学院[vi]
和那些身居音协要职,却写不出一部大型作品(当然这也许是好事)的官方音乐家不同,“学院”在这里是指,把西方古典音乐和官方意识形态、学术-官僚利益体系平衡起来的学院力量。
1984年,《你别无选择》的年代,中央音乐学院的硕士生和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周龙进行了第一场电子音乐会。陈远林(《补天》、《昊》)、朱世瑞(《女神》)、陈怡(《吹打》)、周龙(《宇宙之光》)、谭盾(《游园惊梦》、《三月》)等人当时在列,用的是合成器,用张小夫后来的话说,是在想象中创造了自己的电子乐。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演出。很遗憾他们后来都停止了想象,去学习正宗,否则,也许能发明些新品种出来。
1984年,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合作创建了“计算机音乐研究中心”。1990年,没有留洋背景,上音毕业的陈强斌,又参与创建了上海音乐学院电子音乐实验室。现在他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2003年组建)的副主任。但容易混淆的是,上音另有一个电子音乐机构,同样组建于2003年的“上海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中心”,在作曲系系主任何训田的领导下,担任音乐总监的是少壮派人物,同样师承法系的安承弼。
1985年,武汉音乐学院的刘健创作了《纹饰》,一部为合成器、弦乐四重奏和大型弦乐队写的作品。1998年,刘老师还创作了《盘王之女》,“一部取材于瑶族文化的音乐史诗”,利用了流行元素和商业操作,试图打入市场,未遂,但在系统内部获奖。武汉音乐学院在电子音乐方面的努力一直持续着,1987年,作曲系筹建“音乐音响导演”专业;1994年,“武汉音乐学院计算机音乐实验中心”成立;最近,借着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的召开、《电子音乐创作与研究文集》的出版,武汉音乐学院也开始和法国几大电子音乐中心密切接触,打算成为又一个国际(法系)背景下的电子堂口。
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的陈远林,创建了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实验室。5年后陈远林留洋,电子音乐出现断档,接替他的就是张小夫——1993年,被国家派出去学习的张小夫创建了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电子音乐中心。1994年,张小夫为春晚贡献了开场、结尾音乐,以及集体舞《追日》、《春梦》、《千秋万岁为大年》等配乐,顺利加入了主流文化体系。同年,他还组织了94北京电子音乐周。换言之,他让电子乐在官方、大众、学术这三重体系内获得了足够的地位。而陈远林,现在则以美籍客座教授的身份,继续在中国电子音乐中心任教。
1987年,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龚镇雄教授建立了“音乐声学与计算机音乐研究中心”,后来他写了一本普及读物,《音乐中的物理》(1994年,湖南教育出版社)。他是一个从声学角度研究音乐的学者,并不针对艺术。他做了不少普及工作,比如为中华学习机发明了一套乐理学习软件……顺便说一句,今天中国惟一涉及声音艺术的学术论文,是北京联合大学的“Soundscape——声音景观的研究与应用”(2004)。2005年,中国传媒大学又出现了中国惟一的“听觉艺术”博士生。
2001年,张小夫又发起筹建中国音乐家协会电子音乐学会,两年后该学会被批准成立,2004年加入了国际电子音乐联合会(ICEB), 2005年加入国际计算机音乐协会(ICMA)。这个学会的会长是张小夫,副会长则包括吴粤北(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主任)、刘健(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系主任)。基本上,中国正统学院派电子乐[vii]的版图,就这样统一起来了。
三点三,背景·摇滚
大众的背景只写到1989年,学院的背景则写到了21世纪,这是因为历史在不同领域的影响,并不那么一致。90年代是一个负荷着巨大压力的年代,这压力把反叛的萌芽催化成了地下,将勤勉的顺民疏导到了温室,更使商业成长,以便全民从痛苦的精神世界撤退。在90年代开始的地方,摇滚乐不再是混沌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而是更加孤独,它的“前卫”属性也更加明显。
精神生活终结了,学院派选择了与时俱进,“大众”就向地下和地上分化,向上的一支,就是前所未闻的“商业”。经过数年的学习,1995年,中国第一个流行乐商业化高潮发生,广州乐坛升级,本土歌星走红,小型唱片公司和业余录音棚大量出现。MIDI制作的概念,也第一次达到顶峰。很多几万、十几万块钱攒起来的小公司,在各地填补了商业音乐制作的空白。我记得在1997年,就连兰州都有了几家音乐制作公司,一位熟人,率先掌握了MIDI编写技术,坐在电脑前,虚构着吉他、贝司、小提琴,修改着人声的瑕疵。他坚信真乐器很快就会被淘汰,电脑将模拟一切。我们为此发生过激烈的辩论。人类发明塑料、CD、麦当劳的时候有多么兴奋,他见识虚拟调音台的时候就有多么兴奋。同时,也正是他,帮助实验音乐家王凡创作了第一批多轨录音作品(1997年)。
1990年代中期,中国摇滚乐正在告别流行金属的抒情模式,手艺仍然重要,还没有几个人知道电子乐,即使知道,也限于舞曲。而舞曲是迪斯科的后代,是万恶的娱乐文化,是夜总会,是被假冒芝华士灌晕了的物质男女。1995年,窦唯发表第二张个人专辑《艳阳天》,几乎没有人意识到,电子乐的语言,已经寄生在摇滚乐身上。当时,那种抽离了人性和肉感的音色,让我摇滚的身体极不舒服。制作人张亚东,应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几年,他钻研合成器流行乐、新古典、吉他噪音墙、Drum ‘n’ Bass……拓宽了主流。1996年,和王凡一样,王勇利用MIDI技术和西域宗教资源,制作了《往生》;和王凡不同的是,他还用上了学院派的作曲技术;那是一张没有人能评论的唱片,因为当时没有人同时了解古典、摇滚、合成器和MIDI界面。
1996年,张有待和倪兵发出了影响。有待在北京开办“有待唱片店”,已经开始倾向电子、时尚,但人们还是把他看做北京摇滚乐第一推手。倪兵则在深圳操办“数字之梦”,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推广电子乐的电台节目,开播于1995年。后来这两位都自学成才,变成了中国第一代俱乐部DJ。所谓“第一代”,还有一位要人来自摇滚圈,DJ翁嗡,他曾经是“红烧肉”乐队的吉他手,1996年开始打碟,并参加过崔健的现场乐队。
这些乐评人、电台DJ,都是中国摇滚乐文化的一部分。张亚东也是从这个圈子里出来的,他后来还为“地下婴儿”做过一首电子remix,收录在《觉醒》(1998)里面,那大概是他最后一次玩猛的。当时Drum ‘n’ Bass(和Techno)在北京摇滚圈很流行,王勇的Keep In Touch酒吧,早在1997年初就开始办“RaveParty”[viii];播放Drum ‘n’ Bass和爵士乐的酒吧,当然也不只这一家。摇滚乐,在崔健的时代,是启蒙主义[ix]、理想主义,在“唐朝”的时代,是前卫文化[x];这种激进的传统,让它接纳了舞曲,也接纳了噪音。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前卫”,1997年,我在兰州商学院的讲座上,还把电子乐斥为“踢死狗”音乐,当即赢得了原教旨主义摇滚信徒的欢呼。
好吧,我们已经看到,1995年到1998年,摇滚圈开始接受电子乐。一边消费舞曲,一边创作非舞曲;一边是被摇滚打开了的新生活,一边是延续摇滚的新音乐创作,这个岔路口已经存在,像崔健这种不会跳舞的人,差一点,就卡在当中动不了了。
四点一,跳舞
我们还是从跳舞说起。这是一条没有人梳理过的线索。
“性手枪”和“脑浊”都骂过迪斯科,它有罪。但是2000年到2005年,90%的北京朋克,比迪斯科更娱乐,更没有大脑,这又怎么说?1999到2000年,88号(Club Vogue)、藏酷、Green、Orange、V-One这5个舞场,都是朋克出没的地方,这又怎么说?难道流行就有罪,圈子小就是先锋?
但小众也需要跳舞,或者说,需要集体仪式和身体娱乐。所以,在数年的苦闷挣扎、孤傲愤怒之后,1997年,大批摇滚人被舞曲鼓动。他们参加了有待、Micheal、翁嗡的Party,其中最有象征意味的,是Cheese Beat组织的长城锐舞派对,这是中国第一个DJ组织,主脑就是瑞士人Micheal。1999年,Techno教父德里克·梅来上海、北京打碟,邀请国际顶尖DJ的风气也从此盛行。“Party”的概念不再仅仅是大西、年华、亚梦的摇滚乐聚会,到2000年,“电par”一词也被广泛使用了。朋克、树村摇滚人、国际浪人、艺术家、电影人、文化商人,北京最酷的人都出现在前文说到的5个场地,尤其是头两个。
有待很快加入Cheese,成为主要推手之一,他这样回忆黄金时代:“我们从96年、97年开始,北京一个做Party的都没有……到99年的时候,北京有了ClubVogue,它最开始开的时候就是因为有Cheese party,连续几个周末都爆满。北京除了Cheese,也有了其他的DJ组织,像莲花、HouseNation、中国打气工厂,到99年底、2000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北京跳舞文化最黄金的时候,每个周末都会有Party。当时我就觉得革命成功了……有很多不同的DJ,放不同的音乐,办不同的Party。Cheese是House,然后中国打气工厂是Techno,或者Tech-house,莲花是Trance,不同的人群在周末可以去不同的Party,甚至所有的Party都串完了以后去一个afterhour的Party……”
10年后的今天,舞曲/俱乐部文化再度复苏,却再也没有当年的激进,这中间的曲线,正是外来的前卫被大众稀释,再重新在本土发育起来的过程。革命只成功了一年多,“战士”[xi]们消失了,去流浪,去经商、去上班、去混其他的Party,小众的消费力不再能支撑俱乐部的经营。在文艺青年兴趣转移的同时,警方打击药物,也使活跃分子严重受挫。白领很快接管了藏酷。其后,丝绒、FM等俱乐部前赴后继,但都好景不长;商业舞场的代表Banana却长盛不衰。从1993年兴起的迪厅文化,以滚石、JJ为代表,一成不变地坚持到了新世纪,要不是非典以后,小资开始消费“前卫”,恐怕还会继续一成不变。2003年,有待终于和新兴小资消费群接轨,用九霄-糖果的模式教育了后来的经营者,这个模式,从装修到音乐,到活动策划,都是为领子更白的大众准备的。应该说,今天在工体西门一带发财的老板们,都是从“黄金时代”的肥料上成长起来的。
广州从来都不缺乏商业DJ,像Face这样的场子,也在音乐和商业之间保持着平衡,但是广州深圳两地的市场,连一个倪兵都消化不了,2000年以后,他策划的商业和非活动,主要是在北京、上海发生。新音乐推手欧宁、张晓舟、王磊,也都策划了零星的跳舞活动。
上海没有北京那么多文化传奇,但上海是性感的。从1999年的Club DKD[xii]开始,Techno进入上海,把DD’s曾经铺垫过的俱乐部文化推上新层次。没有朋克捧场,倒是有大批文化商人、社交明星长驻。Park 97、Buddha Bar、官邸、Pegasus等场所的客人,既没有北京的战士那么酷,也没有北京的白领那么土。上海有一个中庸的时尚/小资阶层,他们不需要文化,但他们买单。北京的场景衰落了,上海仍然士气旺盛,作家棉棉从1999年开始办Party,一直到2004年还转战京沪两地,5次来访的PaulOakenfold也到处说:“我爱上海,我爱棉棉”。
四点二,不跳舞
如果说德里克·梅他们是用机器发明了Techno,那么中国的DJ只是在传播电子舞曲而已。在创作方面,似乎还没有多少成就。
A4乐队在2001年发表了《动员日》,他们也是嚎叫唱片的子厂牌“脉冲”的唯一艺人。这是一张聪明舞曲风格的专辑。但A4并没能进入DJ圈,而是在发表第2张专辑,更加纯粹舞曲的《58mm》之后转向制作。人们甚至不知道,A4也曾是诱导社的同伙、丰江舟的追随者。
除了这两个大厂牌,大量独立厂牌在2004年后涌现,Quiet Lounge(广和居)就是一个专注于中日电子舞曲的mp3厂牌。它发行了J.J.e、Red Unit等不知名艺人的作品,大多是东方主义lounge舞曲,尽管影响甚微,但水平整齐。
新一代DJ正在从非舞曲领域渗入,2007年的B6、孟奇、LIman都来自电子乐,甚至实验电子乐圈,他们把笔记本从卧室抱到DJ台,只花了两年的时间。这和MinimalTechno的流行有关,也是因为新的小众娱乐又开始诞生。2005年以来,B6参与策划的AntidoteParty,整合了电子乐手和DJ,从激进风格,慢慢过渡到MinimalTechno为主,在上海形成了新的娱乐潜流。2007年以来,山水唱片的艺人,也越来越多向舞曲靠近;一方面,越来越多人熟悉了Breakcore,并且开始跳舞,另一方面,山水唱片主攻8 bit风格,已经进入了“80后跳舞乐园”的时代。
五,地下
回到1997年,丰江舟一定想不到,Breakcore,或者他所归属的Digital Hardcore(编注,一个厂牌名字,也是这类激进舞曲的大本营之一),居然也是跳舞音乐。这是一个国际亚文化——电子时代的朋克依然是反叛的,2000年以来,比利时的Breakcore Party动辄召集上千人,在归属感和自由的拟像[xiii]中,他们用舞蹈实践了暴乱的快感。丰江舟从乐队转向电子,有两个理由,一是乐队多事,个人方便;二是新的形式带来了新的满足。这也是很多人转型的原因。而且这些人几乎都是地下圈的——2000年以后,因为摩登天空的代理,丰江舟的影响扩散开来,后继者有桂林的周沛(Ronez),他很快走向更激进的硬件噪音,并创立了独立厂牌“豆腐唱片”;还有刚从东北来到北京的孙大威(Panda Twin),他放下吉他后的第一件事,是组建了一个类似Digital Hardcore风格的电子乐队,“挂在盒子上”的主唱王悦担任主唱。这个乐队可能只存在了一天,孙大威很快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他没有那么愤怒。
王凡是另一个有影响的名字。他并没有创作过流行的、独立流行的电子作品。1995年前后,他钻研过合成器,发明了“意识流音乐”这个词,其实是大篇幅的、神秘、实验的歌曲。1997年以后,他开始追求数十轨、数百轨的复合声音/音乐,但他一直没有买电脑,而是用多轨录音机,发明了各种土法,拼接、叠合。在创作了一批电子流行乐之后,他全力投入了声音创作。1999年,他和摩登天空签下一张唱片约,用预付款买了一台Roland VS880录音机,这就是他一直用到2006年的主要设备。后来《身体里的冥响》完成,被公司放弃,中国第一张实验电子/前卫音乐唱片就改由SubJam出版。他的主要手法,是用采样或简单音源,进行无休止的调变,有时还用碎片拼出完整的旋律。他的作品从极暴力的噪音,到简单的高频正弦波,到偶一为之的极简派加新世纪音乐(2002年的《五行》),再到层层叠叠的混沌节奏,都是用那台硬盘录音机完成的。而且,他不懂英文,不读书,对西方当代音乐几乎无知。
王凡的影响集中在地下摇滚圈,杨韬(Yang2)也曾是他的学习者,不少摇滚乐手,都曾在他的超小工作室里听得灵魂出窍(也有人鼻血横流)。在2003年以前,他没有独立的电子/声音表演,而是以大型实验乐队形式出现。
第三个必须提起的,仍然不是崔健,而是王磊。他是中国,而不是广州独立音乐旗手。1998年,他已经从Sub Rosa的实验电子乐中吸取养分,发表了《广州的春梦》(音乐殖民地/龙民),血在民谣,身体是摇滚,但表情却是杂音和错乱美学的电子乐。2000年前后,他组建了“泵”乐队,两年后发表《十个兄弟》(普涞·引擎),这回是暴力的工业电子和Techno。2003年,王磊发表了他第一张电子乐作品,《美丽城》(白天鹅),民族节奏、民乐采样、地方风骨,一张可以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Abstract Hip-Hop作品。2003年底,他又完成Dub’n’ Bass(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词)专辑《馨》(白龙,2004/口袋,2006),然后作为现场电子乐手发展,同时玩雷鬼……王磊的影响在于他的独立态度,而不是音乐制作技术。而且,如果没有王磊,广州就是音乐沙漠。
地下是一个没有系统的场域,它始终没有形成音乐语言上的体系,除了态度就是精神,到达美学,已经是极限。所谓美学,又首先是黑暗、暴力、力量,而不一定是语言革命。当然,能够始终坚持暴力的,也迟早会自成一家。例如“微”乐队的贝司手刘宁,他在2003年发表《我是玩具》(So Rock!出版),又在2006年自制3寸小盘《绿猴子》,行动低调,但从未停止。在地下的谱系中,除了丰江舟身后的Breakcore,几乎没有线索可言,更多的是DIY的勇气,破坏和发明的快感,绝处逢生的运气。这是创造力的炼丹炉,绝大多数,都无果而终。
“微”乐队的鼓手,外号“鼓机”的毛豆,在2001年发表了专辑《粉》(SoRock!出版)。他是无数乐队停滞后,选择独处的地下乐手之一。除了他我们还可以举出黑子(“解散”、“NO”)、曹操(“废墟”、“木马”)、泰然(“修罗”和后来的“阿修罗”)、郭大刚(“舌头”)、虞志勇(“失眠”)……一个太长的名单。毛豆并不是一个好的作曲家,他在一张唱片里塞进了太多的信息,既没有任何传承脉络可言,也没有发明自己的风格。应该说,毛豆和王凡一样,在自我发明,但他不是王凡。
过客太多。陈底里,1992年,他是“穴位”乐队的创建者之一。那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另类/地下乐队,比“NO”、“苍蝇”、“羊皮秋野”都早。1999年,他发表了《我快乐死了》(摩登天空),那是一张既好听又实验,既电子又吉他的唱片。2001年他再发表《疯筝》(摩登天空),就大幅回归了吉他,并且乏善可陈。
胡吗个,人们都只记得“我的外地口音”,听不懂歌词的老外说他是中国的Bob Dylan。可是他在1999年就完成了《一巴掌打死七个》(勾股唱片,2001年),信息庞杂,但妙趣横生的实验、电子、恶搞唱片。2003年他又完成了电子加民谣的《不插腿》(京文,2005)和《柴米油盐酱醋茶》,后者是纯粹的电子实验,拼贴、人声、噪音,除了在姚大钧的《中国声音前线》(后具象,2003)收录过一曲外,从未发表。
Flox。没有人记得他。一定还有无数人和他一样路过。1999年,这位西安的大学生自己制作了《样品: 98-99》,在网上出售,算得上第一张独立发行的电子乐作品。它使用采样技术,简单、业余,但是又有意境……
六点一,不地下
如果说地下是一种文化身份上的选择、建设,那么,作为群体文化,它已经在2003年以后夭折。取而代之的“独立”[xiv]可能更长命,也更成熟。
我们可以拿B6做例子。2000年,他加入了无浪潮乐队“Junkyard”,也就是孙孟晋多次友情参演的那支日式乐队。2001到2003年,B6是两人电子乐队“Aitar”的成员,“Aitar”是受大友良英和欧洲工业噪音影响的“地下美学”典范。这两支乐队都曾在乐评界炙手可热。2003年,B6、cy、SUSUXX、ZOOJOO以临时乐队“ISMU”的名义发表《7.9》(Sub Jam),尽管只用到Cackwalk之类简单软件,但却精准、剔透,在IDM的风格下展开了最大限度的实验,以他们的年纪(其中3人还是大学生)来说,堪称惊艳。2003年,B6和cy的二人组“Dust Box”参加了北京声纳国际电子音乐节,对Ambient House做了巧妙的革新。2004年开始,他发表一系列个人3寸CDR,风格以IDM为主,兼有合成器流行、8bit和实验电子,华丽浪漫。2005年,他开始策划Antidote party。2006年,他和J Jay组成Electro-Pop / Synth-Pop乐队“I-GO”,次年在摩登天空发表专辑。2007年我在上海看到他的DJ现场——久违了的慢热快感。
许多和B6一样的音乐人,出道时在“地下”打磨,成熟后就找到了主流的归属。不知道虎子算不算一个。他也受到丰江舟的影响和帮助,但不是在电子乐方面,而是作为“苍蝇”乐队的吉他手,之后他是“病医生”的吉他手和主唱。2000年,他和一个朋克和一个键盘手一起,组建了“fm3”乐队,并在3个月后退出。两年后他发表了个人专辑《叛客》(摩登天空),借用了“fm3”的素材库,充满数字杂音,但编曲又有强烈的叙事倾向。2004年,虎子又发表了《口痴》(摩登天空),这回是德系极简和杂音风格加上东方空灵。2005年,他和民谣歌手王娟合作了《两个人的旅行》(摩登天空),这是一张相当成功的小资唱片。虎子的本职工作,是新丝路模特公司的音乐制作人。
山水唱片是最能代表独立时代的一个群体。2002年,孙大威创办山水唱片,艺人主要有B6、Dead J、iLoop、ME:MO、nara,大多是80年代出生,用电脑创作的卧室音乐家;后来又和日本8 bit、Breakcore圈子往来密切,有了几位日本艺人。他本人也有了新的化名SULUMI。山水最初是以Breakcore闻名,iLoop至今坚持这个狂暴路线,算是天生反骨。Dead J最初加入过孙大威的Panda Twin,曾经暴力过一阵子,但后来转向虎子式的空灵(《心象》,摩登天空,2005),再转向,就增加了舞曲的成分(《幻术》,摩登天空,2006)。ME:MO最初是自己发行了同名专辑(Fruity Shop,2003),轻巧迷离,相当惊艳,随后才加入山水。nara出道是2006年初,她甜美可爱的风格让人们赞不绝口,目前她和小伟合作。
山水囊括了中国独立电子乐的大半江山,他们从2003年开始和摩登天空合作,一直在努力向大众扩张。2006年以来,已经在年轻一代中打下基础,号召力越来越大,但当初的锐气也随之淡薄了。
2003年出现的Bedzoo厂牌,是由大学生刘伟创办的,艺人和风格都类似山水,但趣味更温和。他们至今只发表了两张合辑。在强调节拍游戏的时候,这两个厂牌都具有潜在的流行能量,随着80后和90后的成长、流行文化的进化,他们将得到更大的空间。
代表了电子乐主流的,还包括插画、动画艺术家古凡(Lowfish),他的风格接近ME:MO,并且毫不逊色;还有类似iLoop的Double Fish,他创办了自己的厂牌“意态重组”。郑州的设计师、插画家巧克力橙子,也在2007年浮出水面,风格也脱胎于IDM。住在北京的新疆青年718的《非攻》(Sub Jam,2005)迥异于同龄人,没有可爱的游戏感,而是大气、老成……随着软件的普及,平面设计和电子乐变成了孪生兄弟,网络游戏也一样,软件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美感、生活圈,数不清的年轻人开始玩电子乐,他们并不把自己看做音乐家,这就是“独立”的根源。
六点二,不主流
早在1993年,宝罗、苏放就曾经创作过新世纪风格的《天堂之花》(宝丽金,1999)。后来他们改走新古典路线,活动稀少。
广州的电子流行乐队“与非门”,在2002年以后开始发表专辑,经过数年独立运作,已经加入商业体系,并自诩“亚洲电音天团”,从此放弃了小众,但大众也没有因此派来大公司将他们收编。
武汉的“跳房子”,在2002年开辟了中式Trip-Hop(我管它叫Chinese Cheap-Hop)的先河,和“星期三的旅行”等乐队一起昙花一现,日后的电子流行组合,多少都借鉴了他们经验教训。
1990年代末萌芽、2002年出头的Hip-Hop音乐,也和电子乐关系密切。一方面,历史上,Hip-Hop对采样贡献巨大,对声音调变、拼贴也有贡献,对鼓机、音序器等硬件也有贡献;另一方面,文化上,它和涂鸦的tag一起,让人类回溯动物撒尿划分地盘的本能,让音乐的身体性强到无以复加。但Hip-Hop也遭到了时尚文化的揠苗助长,像广州的“噔哚”这种坚持鸟味的新乐队,已经不多。
独立和主流之间,如果只是一种梯队关系,就只存在一种文化,和两种状态——阔起来的,和尚未阔起来的。电子乐的兴起,原本是网络社会、小众娱乐、年轻人文化自治的产物,但在庞大的商业齿轮中,迟早要分化为两种文化——终于被大众接受的时尚文化,和终于自成一片天地的独立文化。
七,从独立造音到噪音
卧室革命的起源,是从1998、1999年网络资讯的传播开始。不知名的交流,发生在网络之间,Cakewalk、FruityLoop、Cool EditPro等等免费软件,让年轻人以低廉的成本开始了创作,前文提到的flox就是一例。但因为资讯、交流的不足,单凭免费软件,没法模仿西方已经成型的电子乐,现成可以学习的,只有半合成器流行乐,半电子流行乐的国产MIDI经验。所以,2003年以前,可以看作是电子场景的酝酿阶段。前文说到的独立电子乐,当然也在其列。
同一时期,姚大钧的前卫音乐网、且歌的声声慢[xv]、网络乐评人Acid Rain,都专精于前卫和实验。尤其是前卫音乐网,第一个系统地介绍了摇滚乐以外的新音乐,也让人们知道了学院派电子乐。1999年,李皖发表在《芙蓉》上的长文《电子,声音的一切可能》被年轻乐评人李如一指出“抄袭”,这也意味着二手资讯的时代行将终结。王长存、徐程、hitlike、k1973、杨韬、李如一等人都受到了姚大钧的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过乐队经历,从软件开始创作,也不受类型电子乐的束缚,直接从探索、试验开始。这些人在2003年的北京声纳音乐节后开始活跃,今天已经是前卫、实验的主力。
老一代实验乐手,像王凡、李剑鸿、欢庆、Junky,都是从音乐过渡到声音,从硬件开始创作,多数具有“重新发明”的特点。王凡最初使用自己发明的声音合成、调变方法,他从2006年开始使用软件,仍然基于类似的创作原理。李剑鸿是噪音吉他手,在2005年组建了硬件噪音乐队Acidzen。他、周沛,更晚出现的洪启乐、兼跨软件和硬件的徐程、从乐队转型的Junky(他和徐程组成了著名的噪音乐队“虐待护士”),都利用效果器制作噪音,在文化和美学上,是激浪派和朋克的后代。“fm3”更复杂,组建之初,受Minimal舞曲影响很大,2002年以后确定了极简实验氛围的风格,并且以中国传统美学为标志。2005年他们发明唱佛机,把电子乐拉回了最低的技术指标,在国际独立电子圈造成轰动。2007年,又回归长音摇滚传统,变成了地下摇滚明星的新模样。
在北京,忽略技术背景,混合音乐和声音的做法相当普遍。曾经是工业摇滚乐队成员的冯昊,在2003年创作了《声音》,一张粗糙的极简节拍电子作品。现在他既是吉他手,也是电子乐手。曾经是上海第一代实验乐队“布拉格之春”成员的Zafka(张安定),2004年底开始声音创作,现在他主要作为声音艺术家活动,从音景创作,到社会学调查,兼玩后摇滚,兴致颇广。我和武权都是从2004年才开始创作,我从田野录音入手,用GRM Tools插件处理声音,武权用Reaktor软合成器制作声音和音乐,从原理上说,都在利用电子原音的遗产。
如果我们把“实验”和“前卫”区分开,可能会有点意思。实验的重点在态度(1960年代以来的音乐创新传统),前卫的重点在学理(1910年代以来的艺术革命传统),哪怕是自学的学理。姚大钧在最近10年的贡献之一,就是让中国当代音乐终于开始讲道理,从历史传承、技术文化,到美学和资讯。在所有人都在笼统地使用“实验”的时候,他使一些人,深谋远虑地赋予了“前卫”新的意义——它不只是一个形容词。
同样没有音乐背景的8GG(八股歌),用自己开发的软件平台工作,对网络艺术、媒体艺术、声音艺术、VJ、互动艺术都相当精通,他们不属于年轻一代,也不热衷于网络交流,既不在艺术圈,也不在音乐圈,是一个特例。2001年,他们用记录网络声音的方式,创作了《网上音景》,可以看作国内最早的声音艺术作品之一。
对大众来说,有节奏的才叫电子乐,实验电子乐应该叫噪音才对。实验领域的电子乐在技术上更接近传统电子原音,在概念上更接近艺术[xvi],这也是噪音盛行的一个原因。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只是种种声音现象之一,那么,电子乐自诞生之日,就意味着探索声音的无限可能,而不是戴着镣铐跳舞。这些迟到的噪音,对大众来说还难以理解,对“和谐”审美的神话来说,更难以容忍,因此,“噪音”就不只意味着对声音的纯粹聆听,也构成了政治学的隐喻[xvii]。
八,分享未来
2000年到2003年,独立策展人李振华一边推媒体艺术,一边推电子乐。他左手是“fm3”、“超级市场”、丰江舟、“塑料大龙”、虎子这些电子艺人,右手是乌尔善、汪建伟、8GG、赵亮这些媒体艺术家,腰里还别着一群DJ。这种宽泛的“电子文化”的视野,在西方和在中国,都有一种前卫/时尚的对应关系。2004年秋天,侯瀚如策划了第2届“白夜”艺术节,有100多万巴黎市民参加了这场狂欢,我和“fm3”、武权在一群DJ、VJ之后表演,隔壁是李剑鸿、王长存、钟敏杰、兹比格涅夫·卡科夫斯基,楼下人头蹿动的入口处,是Sensorband长达12小时的噪音巨浪。这是究竟是社会性的文化共生,还是消费文化吞噬一切的容量,还需要连篇累牍的讨论。
在西方,因为文化政策的倾斜,实验电子乐、媒体艺术比较容易得到资助[xviii],在中国,塑造科技神话的进程中,也开始有资金流向高校和官方机构。2004年,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中心把“电子音乐周”升级为“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每年一度;上海也从2005年开始举办电子音乐会(“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2006年升级为“上海国际电子音乐周”;武汉音乐学院则开始筹办“2008武汉国际新音乐节”,其主题就是“纪念中国电子音乐专业教育创建20周年”。这些活动的共同特点,就是在学院内部消化,尽量不让外人知道。2007年的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筹备期只有3个星期;早在1999年,北京的约瑟夫·冯自费筹办“ICMC国际电脑音乐节”,对公众来说是个秘密,这是官僚-教育体制的通病。
2007年的上海电子艺术节,主办单位是有学院背景的艺术机构,可能是惟一在官方、学院、社会几方面取得平衡的活动,既满足了上海式官方活动的排场,又给了学院派入世的机会,也吸引了大量来自豆瓣、新茶、Last FM的年轻人,媒体报道更是一片溢美之词。这个模式想必会被借鉴下去。电子音乐、影像在大众面前,始终是《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一个又一个新版本,约瑟夫·冯夫妇的公司,这些年没少为跨国公司制作大型公关活动,像“神五”庆功、财富论坛、奥运会,也都少不了他的“电脑音乐”的装饰,高端市场的购买力,应该会感染到大众市场。至于人民是否需要电子乐[xix],需要什么样的电子乐,官方意识形态,又如何渗入电子乐与时俱进,将是未来的话题。
在整个教育系统里,除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几乎没有任何当代电子音乐资源。电子音乐,被当作秘密武器来研究,这似乎不符合教育系统的实利主义主旋律。但在市场的召唤下,几乎所有的艺术院校、系所,都设置了媒体艺术、数字艺术、电子艺术专业,尽管除了动画,几乎什么都不教,但相信很快会从国外大规模引进师资。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中心的美籍教授艺科(Kenneth Fields),对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贡献不小,也在学院和非学院间充当了中介,把教授拉到酒吧演出,把噪音人带到大学讲课。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系的张培力,从2005年起引进了姚大钧,每年请他短期授课,2007年,学生们甚至举办了自己的声音艺术节。
学院、商业、实验/前卫、市场和文化、国际化……更多的融合、交流,更少的自我发明。在这个信息过载、没有系统的国度,一切成长都是新的。西方的历史已经发生过,不会再次发生,我们既不可能复制西方,也不要以为土法炼钢真的可以实现革命。电子也罢,电脑也罢,只要不停电,我们都将继续废话下去,冷暖自知。
注释:
[i]本文是2004年《废话的语法——电子乐和中国电子乐》的升级版,完成于2007-2008年,原载《音乐时空》杂志。该文收录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溢出的都市》。“废话”之意,指电子乐对传统音乐追求“意义”的美学的放弃。本文没有涉及港澳台地区,严格地说,应该是“中国大陆电子乐”才对,特此说明。
[ii]本文中所说的磁带机,是指1930年代发明、1940年代末期应用的老式开盘录音机(tape),而不是家用盒式卡带(cassette)。
[iii] Cakewalk是在国内流行乐领域最早成为必备工具的音乐制作软件。
[iv]官方,official,这个词首先是1980年代以来,汉学家在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中大量使用的,它的对立面就是所谓的民间诗歌运动。这个词关系到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生产的基本权力结构,在中国当代的文化、艺术语境中,有着关键的意义。
[v]“e化”台湾,是台湾近年来的科技/经济发展策略,意思是发挥电子技术优势,通过软件、电子、科技产业来推动经济发展。相关的音乐、艺术、文化产业也因此被政府看重。
[vi]此部分资料大多来自二手,未经田野调查,虽经反复查证,但难免有遗漏和错误。特向读者致歉。
[vii]关于“正统”的含义,参考关于“官方”的前注。
[viii] rave party是1992年前后,从英国扩散至其他国家的地下跳舞活动。药物和音乐具有同等重要性。通常在室外或厂房举办,因而很快被立法禁止。随后转向室内,才有了所谓俱乐部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并不存在rave。这个词的流行,是我们对新、边缘、叛逆的想象,“锐舞”、“瑞舞”在媒体上的流行,很快证明了这一点。
[x] 90年代,前卫美术圈对摇滚乐的态度相当友好,很多人把摇滚乐称为“前卫艺术”,但这种说法更像是文化上的修辞,而不是学术上的认同。
[xi] Party圈的“战士”,和摇滚圈的“铁托”一样,是气氛的灵魂,这些战士从无业游民、朋克、地下艺术家,到网站CEO、摇滚圈前辈、服装店老板,职业不同,但都能以全部身心让周遭环境变酷。“战士”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不需要买票。
[xii]英文“颓废杀死沮丧”的缩写。
[xiii]“自由的拟像”是从鲍德里亚那里抄来的。
[xiv]这一部分说到的“独立”,既是音乐类型上的“独立电子乐”,也是“独立音乐”、“独立厂牌”灵魂所系的独立精神。所以,某些貌似很新,很“indie”的电子乐,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xv]且歌创办的“中国音乐第零网”和“声声慢”网络杂志,是第一个集中介绍前卫音乐、实验摇滚的内地网络资源,后来且歌神秘失踪。大约在2006年,大部分的内容被网友收入《独立不完全参考》,继续在网络上传播。
[xvi] 2006年我写了《背景——声音艺术在中国》,刊登在第14期《今日先锋》(世纪文景出版集团,2007)上,也可以在我的博客上找到。关于实验电子乐,在此文中有更详尽的论述。
[xvii]参看雅克??阿塔利的《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第一版。
[xviii]可以大概说: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是娱乐,实验音乐、即兴音乐是艺术,所以前者归市场管,后者归政府。但这只是趋势之一,各国文化政策之发达,之不同,远不能概而括之。此外,电子、数字、媒体文化牵扯到“高新技术产业”,所以也容易得到政府和企业(例如日本的NTT、SONY)的支持。
[xix]根据北大龚镇雄教授的文章,早在1990年,东方歌舞团就已经公开举办了“计算机音乐会”,此事甚为蹊跷,待我修订本文再做打探。